访谈时间:2023年8月
访谈对象:D
生活区域:西南地区
个人标签:女权主义者
年龄:90后
访谈时长:266分钟
(出于受访人的安全考虑,文字稿有删减100分钟左右的内容)
访谈人:小A
校对:Chris, 鸽子, 小A
2020:「我爱我的邻居」
对于疫情最早的印象是什么? 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事情发生了?
其实昨天大家闲聊的时候,说到一点点…我听的时候都感觉很创伤,这个创伤的感觉现在日常不会直接地感觉到,但是每一次直面、偶尔聊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难受。
最早我觉得是大年三十那一天。其实那之前武汉本地就有很多的说法,外媒上也是说有的,但是国内所谓主流媒体就是很迟才承认这个事情,反正是大年三十那天晚上还没有承认,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我那天晚上就感觉很痛苦,我是相信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是家里人他们年纪比较大,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渠道,也会觉得说「国家也没有说啊」、「你看这大过年的,你不要想这种事情嘛」。他们还在客厅里面看春晚,我就觉得很受不了,没有办法看那个场景,我就在自己房间里面呆着。
你看到春晚上面也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戴口罩的,那么多的人坐在一起。虽然可能当时北京没有病例吧,但是你就会觉得特别荒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怎么没有任何的重视?
那时候你是在老家?
是在老家,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出国读书,因为那边关闭了边境,就休学了。
疫情那几个月特别焦虑,每天睡不着,很晚很晚都睡不着,一直在刷相关的新闻。当官方承认之后,新闻是可以被报道了,你就看到所有东西都是没有希望的。首先这个病当时治不了,然后物资是缺的,医疗资源也是缺的。当时国内刚刚爆发的时候,很多地方也会给武汉捐物资,我们还有一个留学生群,大家做了募捐。
当时真的吃不下睡不着,特别焦虑。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什么,而那些「你觉得他应该去管理好这个事情」的职能部门,他们也做不了什么。只有参与到一些小组去做事的时候,才没有那么焦虑。我不是那个留学生的捐助的发起人,但我在网上看到后有进他们那个群,帮忙收集一些信息,也发朋友圈问有没有人想要以留学生的这个身份,来给国内捐助。那个时候国外其实还没有爆发疫情,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要为我的这个所谓国家或者说我的同胞做一点事情。
当时还有在其他的小组做事。有一个小组,他们最早也是针对疫情的状况对接物流、对接床位、对接病患信息等等。
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那段时间都是跟我一样的状态,有很多人都自愿加入到这些小组里面帮忙。这个小组我加入的时候是相对有一点晚了,他们可能已经做事做了有几个月了吧,当时已经没有那么急迫地要去收集或者筛选很多信息。我观察到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值得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有去做一些采访。除了我自己所在的小组外,也有采访别的小组在做的事情。
当时有采访一个小组,是有人在豆瓣还是哪里发起的,它的slogan是「我爱我的邻居」。它并不鼓励大家面对面地去交接物,而是提议你可以把多余的口罩送到别人家楼下的快递柜等等,你跟邻里之间有建立这样一个bonding、互助的感觉。也包括如果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有去医院的需求,你也愿意承担一定风险去接送,或者你可以作为求助人在群里发出求助,看谁有这个意愿和能力来帮你。它不会鼓励你要牺牲自己,而是在保护好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去帮助他人。
还有采访了另一个小组。我当时采访了小组里的三个人。有一个女生当时做的是那种特别紧急的物资对接,就是可能需要二十四小时在线不停地看消息,去问医院你们需要什么。因为可能这个时间错过了,这一批物资就没了,或者时间延误后,病情可能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还有一个武汉的朋友,他当时也是自愿加入进来,帮忙做了很多调度。他同我讲,在武汉当地,其实更早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传李文亮医生群里的那些截图。年轻人会更警惕一点,他当时就想跨年元旦的时候就不出去了。他们公司人蛮多的,他开会的时候也会戴口罩去,但是当时很多人没有当回事。
这样的小组会通过什么渠道去对接那些医院呢?都是由志愿者构成的话会不会有管理组织上的混乱呢?
在留学生募捐那边,我们当时好像是有筹到口罩还是防护服之类的,用很原始的办法,去网上查。网上会有人发医院的联系电话,以及医院需要什么。你就给他们打电话,问他们需不需要物资,如果需要的话能不能加一个微信,看你们需要多少,我们能不能找到物流把这个送过去。
我觉得可能很多小组也都这样。当你开了这个口子之后,医院的人会再把这个信息转出去。当时我采访了那个做了很多物资对接的女生,她就是会把每一个捐助人和受助人拉一个群,所以她当时拉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群,这样大家可以更直接地沟通,也会更公开透明,医院有时候也会写个感谢信之类的。应该主要都是这样网上对接的。
还有一个小组,是一个社创平台。他们主要是对社会创新的很多东西感兴趣,每年会不定期地招募汇集一群很关心社会创新、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年轻人。他们当时是想做一个对疫情的民间观察的记录,最后出了一个报告,我当时也参与了一小部分的工作。它的报告有接近一百页吧,分了不同的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当时好像研究的是,民间小组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怎么产生的,我都有点记不得当时具体内容了…
当时在小组里认识了很多朋友,跟其中一些人会相对更紧密一点。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女生,我们做了另外一个关注性与性别的平台,也做了一些线下工作坊之类的事情。
我们当时还做了好几篇从性别角度对疫情进行科普的文章,因为疫情爆发后,世界各地的家暴数量和比例攀升得非常快。我们做的家暴科普,就是先破除大家对于家暴的刻板印象,以及讨论疫情当中,家真的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吗?
之前几年 WHO出的一个报告,是关于医疗行业内的性别差距,那个报告的名字就叫「led by men launched by women」, 做事的是女的,leader都是男的,其实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子。我们就选取了报告的一些部分来翻译,医疗行业内的职场晋升、工资、性骚扰等等,当时就是把这些重点的部分拿出来翻译,做了一篇文章。
我会觉得当时参与这些小组的过程当中,会让我感觉好受一点吧。就是你知道你这些信息是可以传达出去的,是可以帮到其他人的。
这些小组、组织,这些报告, 应该都发生在疫情最初期2020年?
对。
它有缓解你当时的焦虑或者痛苦的感觉吗?
我觉得没有完全,但肯定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再来一次,我肯定还是会去做那些事情。
因为我现在回想到,当时整个人确实就是一个非常抑郁的状态,做事的话会稍微好一点,至少和你当时那些做事的朋友产生了直接的沟通,你去推进某一个采访、去排版、去编辑、去找资料的时候,注意力是被分散的。现在回想会意识到,在当时就是应该要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比起什么都不做,至少是要好一点的。
三四月份新冠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你们的工作重心和想法在全球爆发前后有什么变化吗?
后面国外开始叫所谓的「China Virus」、以及国内对留学生说「不要千里投毒」。其实WHO以及很多国际组织,那个时候都有呼吁说不要用这种歧视性的称呼。在之后参与的一些小组里,其实是有根据疫情的变化分组——物流组、后勤组、和科普组之类的。科普组他们会去翻译这些资料,也去做一些比较深度的科普—— 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中国肺炎」或者「武汉肺炎」等等。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受——其实那个时候, 我甚至还在考虑要不要出去继续读书,这个事情都没有决定的。我忘记了前后的时间线,我记得当时有一条新闻——一个华裔女生,可能也是中国人吧,在我读书的那个国家首都街头被揍了。当时我朋友还跟我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到那个 city library那边, 做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表达,反对这种种族歧视、针对亚裔的仇恨,我们当时还有在讨论这个事情。
疫情初期你在什么区域?当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在老家, 长三角的十八线小城市。疫情这个事情确实严重之后,全国可能都有一段时间是限制出行——不是说完全不能出行, 他也给你发出门条,但我真的可能在家里待了有两个月没有出门。我爸是公务员,他有时候要出去值班。当时也有那种恐惧——我不知道他回家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带有一些病毒。因为家里还有爷爷奶奶,跟老人一起住也会很担心他们。我爸当时每天进门,我就说你先在门外,我给你喷酒精。他每天一回家就先把外套都脱了,脱了之后挂在阳台上,喷消毒液。
家里的口罩,我记得那个时候口罩还没有断货,我是在网上抢到了一批。但是后面我爸妈他们想再买——他们的那个信息肯定是比我滞后的——他们想再买就再也买不到了。
你对李文亮这个事情有印象吗?
有印象,我当时就非常生气非常愤怒,在朋友圈狂转了很多东西。当时也会给我爸妈转一些相关的东西,当时还有个视频,据说是在武汉,在《吹哨子人》那篇文章过后,有人拍对面的楼,所有人都在家里,没有人说话, 但是有哨子的声音。我对那个视频印象挺深刻,就很难受。包括《吹哨子人》那篇文章,我当时是把它念了一遍,做了一个音频发出来,但是后面好像也不能再转发了。
李文亮那个事情是很痛苦,存了很多截图,发了朋友圈,但是那个时候发现有一些东西,朋友圈里发出来也没有人看得到。我爸他们肯定也都知道了,哪怕他们不上网、不看微博什么的,他们都知道李文亮的事情,至少在李文亮这个事情上,他们没有办法再掩盖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好像是接近12点的时候,说他已经去世了,又有官方消息说他没有去世,在抢救,说「你们前面说他去世的都是谣言」之类的,又开始变成争论点。当时所谓的「领导不让他死」、 「你不能这个时候死,至少要展示我们尽力了」这样的一个姿态,也让人觉得很荒谬、很难受、很痛苦 。
你觉得当时自己焦虑的更多是哪方便的事情呢?病毒的危险?自己的生活?学业?国内的公共卫生管理?
那个时候都没有太担心学业,反正我已经决定休学,并不是在焦虑于出不了国这件事。但是每天你看很多很多的新闻,就是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明明最开始就是有人提醒的。我觉得到现在他都没有承认「我们在最开始没有做好这个管理」,没有向大众承认这个错误。
你看到那些,你看了也没有办法去帮忙的求助,也会觉得特别无力。还会有很深的愤怒吧—— 对公权力的愤怒, 就是觉得说,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最后变成用普通人的生命去填补你们自己的错误,还不让人说话。
也有很无望的感觉——这样的事情就像一个放大镜,把每一个层面的事情都暴露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没救了。当时也看了很多纪录片,那个时候还没有关于新冠的纪录片,就看讲述人类历史上的大流行病的纪录片,有讲到非典,当时我还拉着我爸一起看。
那个纪录片里面也说,这种大流行病就是会不断地再出现,人类是没有办法管控住它的,人类必须要去做更多的准备——不管是公共卫生、还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会觉得人类真是没救了。
你当时有很强烈的对于公权力的愤怒感,但是你的父亲他自己也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那几个月的时间里你会跟你家里人聊起这些事情吗?会有一些张力存在吗?
我觉得我没有跟他直接有冲突,可能到现在也没有直接地和他去聊过我对公权力的态度。我觉得2020年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把这种愤怒直接地指向我父亲,反而是疫情后面几年,国内持续了三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确实意识到…
我在内心会觉得,假设我过去三年经历过的那些被「喝茶」的经历,是公权力对我的强奸的话,我爸就是按着我的手,让他们上我的那个人,我有产生过这样的感受跟想法。这个感觉会让我意识到,我不可能再跟我的父亲进行这种深入的探讨了——你可以去进行,但是一定会是痛苦的,我不想经历那个痛苦了,你意识到自己是没有办法跟他达成共识的。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难受的点就是,这个国家的管控的方式入侵了我的小家庭。或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至少我的父母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后来我意识到,他们确实可能知道一点,但是他们不可能像我那样程度地去批判和去痛恨,他们还是会有很多他们没有办法绕过的、他们自己的issue。在我还期待他们能理解我的那些时刻,我觉得很痛苦的是,为什么我的小家庭要被入侵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们最后变成了我的「国保」?我会更深地痛恨整个审查,他就是侵入到人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不仅是亲情,甚至是爱情或者友情。
前几天朋友们还说看到那种小学生现在上的课,什么「国家安全反恐教育」,就是跟小孩说——你也要注意你身边的亲人,他们每天在讨论什么,如果有任何异常的东西,你要及时劝他们「迷途知返」。
我对这些东西的忍耐程度变得越来越低,以前至少我觉得我跟家人之间的信任是在这儿的,经过这几年的这些事之后,我觉得这份信任可能打了对折,甚至就已经没有了。
如果我没有找到现在身边的这群朋友,在任何主流的场域里面,我都不会感觉到安全——你不知道这些人的政治态度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过反思,或者他会不会对你的一些言论有怎么样的看法。
人必须时时刻刻地想到这些问题,已经失去了对他人的天然的信任感。
是的,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这样是正义的」,这样就很吓人。
你当时在家里两个多月没出去,但做了很多事情,它有缓解你当时的焦虑或者痛苦的感觉吗?
我觉得没有完全,但肯定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再来一次,我肯定还是会去做那些事情。
因为我现在回想到,当时整个人确实就是一个非常抑郁的状态,做事的话会稍微好一点,至少你当时那些做事的朋友,产生了直接的沟通、去推进某一个采访、去排版、去编辑、去找资料的时候,注意力是被分散的。是真的觉得你输入了一些知识,然后还可以把它输出出来。
现在回想会意识到,在当时就是应该要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比起什么都不做,至少是要好一点的。
疫情刚爆发那几个月出现了很多民间互助的组织。当时也有人在讨论,在一个不断收紧的大环境里,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刻,大家看到了突围的缝隙。对于你来说 ,你当时会有这个意识或者那种感觉吗?
可能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意识到以前有一些事是不能做的,但是当时我会觉得所谓的「上面」,它没有办法去阻碍这些民间的自助,它的行政资源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这种管控了。我记得我当时有很强烈的感受是,最近产生的这种交流沟通,都是跟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去产生的联结,这种联结是有意义的。
我当时发了条微博,大概意思就是,这是我唯一信任的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在这样的状况下,跟一些具体的人去产生互助的这种关系,是我最受用的、也是我最信任的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包括我刚刚说,我们后来做的那个性别小组,大家最开始也是在疫情民间小组里认识的,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后来很重要的朋友。
2020年这一次,你是什么时候走出家门的,有印象吗?
翻一下我才记得具体时间。但是我当时走出家门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过了很久,以及确实很喜悦的感觉。虽然你会知道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去喜悦,因为有很多的伤痛已经发生了,但是确实就有一种「被放出来」的感觉。
我记得那一天是我跟我爷爷奶奶下楼散步,还戴着口罩,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油菜花已经开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的,一片全部都是那样子的,上一次出门的时候还是冬天的感觉,再出门的时候,油菜花已经开了。
后面我就没有在家里待着了,六七月的时候我就出来了。我记得可能也是那个时候, 我爸妈就跟我说,「你不要跟一些所谓网上的人有过多的交流」。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我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跟他们有太多的交流,每天半夜在那跟人打电话,他们会觉得你在搞一些危险的东西、敏感的东西。
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当时留学生捐助,我有跟他们说的,我家里人还通过我捐了一些钱,他们是有很朴素的正义和善良,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去批判很多东西。
我觉得也跟他们受到的教育、所在的年代有关,他们是会有更多的恐惧。
2022:被破坏的一切
22年下半年封城封了有20多天吧,我在那个期间打了很多次电话,解封之后还一直在打电话,打了很多次12345市长热线,但是没有用,几乎每一通电话都没有用。 当时还跟楼下的物业吵架,跟那个志愿者吵架,但是都没什么用。
当时就是不想下去做核酸,他们上来敲门,感觉要把你家铲平了那种气势。我先打了12345,一开始投诉会跟他们掰扯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问题,包括给他们读法条,什么《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隐私法》。其实这种要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隐私信息,你是需要有合法合理的理由和渠道的,我们的核酸是收集我们的RNA信息,他需要征求当事人的书面同意。
你是因为不想做核酸所以收集这些信息?这些电话一般打得通吗?对方什么反应?
电话很多时候要等很久,打通了之后就给他们念法条,我觉得我至少给20个接线员念过法条——除了你的书面同意,还要告知当事人他有「无条件拒绝的权利」。核酸收集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这些所谓社区工作的这些人,他们是没有执法权的,而且他们的态度特别不好。
我还投诉了人脸识别,有些小区的人脸识别会直接显示出你的健康码信息、你什么时候做的核酸,很吓人,有一些商场是直接在公开场合,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地方,显示甚至播报这些信息。
我说我可以配合防疫,出示这些信息,但是一个物业公司一个商场,这些民事主体他有权力使用这些机器吗?这个后台这些信息会进入到哪里?这个机器已经上市已经投入使用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公司有权力去生产这样的机器,经过了怎么样的评估和信息公开的流程,就投入了使用。我说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隐私信息,我不知道这些公司背后有没有境外势力想收集我们的信息。
(笑)
一开始我就给他们掰扯这个政策的问题,后面发现谈政策,他们就不会跟你进入到任何具体的对话当中、观点的交流当中。他们会把工单派到街道那边,可以在12345的那个网站查到自己投诉的内容——有一个流水信息是他处理到哪个步骤了、哪个部门在管理了。有些时候根本没有接到街道的电话,它就已经显示说「已与当事人沟通处理这个问题」,有时候他的回访电话就响一秒就挂了,你都还没来得及接起来,挂了之后这条投诉又算结束,他们会采取这种回避的方式,让你结束所有的这个流程。
后来发现,你跟他们争这个政策是没有用的,他们没有这个发言权,他们只会说「我们会向上级反映」,「在处理了」之类的。后来我就会投诉他们的工作态度跟他们的工作方式,比如敲门敲得像要把门砸掉似的,比如不介绍自己就让人要配合等等。
我打过一个投诉电话,给街道办的接线员一顿输出,那个街道办的人直接就把电话挂掉了。我再投诉的时候,就会投诉这个人的态度——居然敢挂我的电话。后面我开始投诉工作方式跟工作态度,一般都会提出我的诉求。因为你投诉之后,如果没有具体直接地提出你的诉求,也不太会有处理,我这次投诉就说,至少让这个接线员给我打电话道歉。
后面他又给我回了个所谓的道歉电话。他那个道歉也不情不愿的,他说「你有什么诉求」,我就说「你念一下我给12345写的单子里面,我有什么诉求」。他开始念,我说「所以你就是来打道歉电话的,那你开始道歉吧」。
他说很抱歉上次挂了你的电话,我又给他一顿输出,开始反向PUA,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吗?」。我打了三十通电话,最后就收到这一个道歉,但没有用,他也没有任何权力。
中间封控那段时间,我不想下去做核酸,他们还让一个民警过来了。我就跟民警说,他们做核酸的每天在下面吼,我每一天都精神衰弱,我月经已经推迟了两个星期了,我下不去楼。我就顺势坐在地上说,下次要做核酸,我要求给我上门做核酸,我现在一层楼都爬不动,跟你说话都累得不行。
(笑)
我记了那个民警的警号,找了四张A4纸,把它们粘在一起变成一张很大的纸贴在门口,说「我已经跟警号xxx的民警沟通过,因为个人身体原因要求上门做核酸,请不要在九点之前敲我家的门」。但是也没有用,他们第二天又来了,来之后又吵了一架。但是我那个纸就一直贴到解封,都一直贴在门上。
小区物业和志愿者,他们每天在楼下拿大喇叭喊一整天,本来可能早上八点开始,后来越来越早,七点多六点多开始,一直在喊做核酸。他是按一栋楼一栋楼,一层楼一层楼,这样的顺序让你下来做核酸,他就会在那不停地喊,拿那个大喇叭反复在那放。
我就说我已经投诉扰民,不排除后面我会追究法律责任,本人会看心情起诉之类的,贴在门上,但是其实也没有用。
我的窗户是可以直接看到核酸点的情况,有一天在楼上看到有一个人去排队,过了一会他又来排队了,我后来就意识到他们家所有人都把手机给他了,让他去做很多次核酸。这个东西根本做不到所谓的精准防控,你不知道这个数据掺水的成分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多少,特别可笑,这就是你说的精准防控吗?
你当时打那么多电话,你自己也知道没有什么用,为什么会一直打?
我就是觉得特别生气,我每次想到这些事情就特别生气。但我又不想把这个怒气发散到我身边的人,比如说我的同事、朋友身上。
后面我就跟接线员说,你应该读过一些10万+的文章吧,你应该读过那种路过一下被拉去方舱隔离,那种人写的10万+的个人自述吧?我说我的每一篇公众号文章都是10万+阅读量,你们街道想火的话,你们城市想火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一把,你就这样跟你领导说。
我还说,我知道你是接线员,你没有权力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你对这个政策也没有改变的权力,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不相信你没有在下班的时候跟你的朋友吐槽过这些政策。 你自己想一想,你从来都没有觉得这影响了你的生活、你的便利吗?
我就这样,想各种方法、各种角度,去跟一个被要求只做机器的人去进行沟通。我记得有一个女接线员,她还有一些人味,她说,是啊,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有很多不便。如果是男接线员,很多时候他就是沉默。
投诉人脸识别的机器的时候,我说那个市长也每天做核酸吗?他自己家没有老人吗?没有小孩吗?那个时候我有朋友家小孩发烧,很小的小孩,不到一岁。去医院,医生说所有的人都要有24小时核酸,就不让你进。我说,这些疫情防控的干部,他们没有家人吗?没有小孩吗?家里没有老人吗?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绿色通道呀?市长他到了商场,一个没有任何执法权的保安要登记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居住地址,他会登记吗?这些人他们过的是跟老百姓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制定这些政策时没有想过带来的生活上具体的不便吗?
但是几乎没有用。我觉得就是得不到任何回应。
那个时候你会有那种物资抢购困难之类的情况吗?
这个倒还好,我之前就已经买了很多东西,家里也会有一些吃的。上海封控的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焦虑,当时就已经下单了一些干蔬菜、罐头之类的,一直放在家里也不会吃。三月看到上海封控的时候,就被带入了那种焦虑的感觉。我还收拾了那种拎着就可以入住方舱的那种包,里面有日常洗漱用品、 一些巧克力、压缩面包之类的,还给猫打包了。
当时养了三只猫。我也进了宠物互助群,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里面互相帮忙。当时是有一个小区被拉走进方舱,那个女生她就是不愿意走,特别担心她的宠物。
其实我们那边当时有出一个内部文件,说不可以扑杀宠物,但是内部文件不会公开出来。我后来就打了农林局的电话,一开始没接,结果半夜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个人的电话号码。感觉他是一个值班人员,至少这个人的态度还蛮好的,他就跟我说,「我们是有一个内部文件,肯定是要求不能扑杀宠物的,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小区遇到类似问题,你们也可以直接现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你跟民警沟通」之类的。至少这个人的态度还可以 ,我当时还录音了,把那个录音发在群里面,但也不知道那个女生后面怎么解决的。
大家也都给她出谋划策,如果宠物不能带着隔离,那至少小区要统计好谁定期来上门喂,钥匙有没有留好,不能让宠物跑出去,消杀的时候这个事要有人负责。我们当时也有讨论,如果真的到那种他要把你拉走,把你家全部消杀的情况,我们把猫放出去,让他们去做流浪猫,都比交给到什么宠物隔离的地方去更好,我不相信这些人能把你的猫照顾好。
那一个月我真的在门口玄关上放了一把刀,厨房的菜刀。我就想,要死一起死,反正谁他妈要直接拉我走,要对我的宠物做什么,我就直接砍了,大不了上新闻,谁怕谁?这辈子还没上过热搜呢。会想到这种程度,每一天的精神压力就是这样子。
当时本地有那种特别恶性的防疫事件吗?
不能说没有吧,但总的来讲,没有爆出来像上海那种直接把宠物打死的事。我觉得可能这个城市也没有上海那么自信,或者没有那么多的钱,它也不会想把事情闹得特别大。这里总的来讲还是比较中庸的,在维稳这件事上,比较中庸。
反正当时在家真的特别难受,真的要发疯。你虽然是在家里面,是你熟悉的环境,但是除了这个环境之外,所有的环境都是被破坏的。你没有办法按自己的意愿出门或者不出门,我可以自己在家宅二十天,但是这个是我选的,那二十天不是我选的。每一天都有人在你家敲门,在你家楼下喊,把你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对待,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想砍人。
解封之后我去上班了。我们公司当时是在另一个小区里租的楼。有一天刚吃完午饭、准备午休的时候,有一个同事突然在工作群里面说,我们小区只进不出了。我去小区门口,那个门已经被物业的人拿自行车锁锁起来,所有人都不能出去。门上贴了一个说明,上面有三个座机电话号码。我挨个给他们打,发现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电话被写到这个小区门口上,我说你立马给我过来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小区被封了,你们三个的电话在上面。
我现场也立刻报警了,打了两次报警电话让警察过来。我就特别生气,一下子被trigger到(被封控的时候,跟那些人吵架的状态),在现场就直接跟那些人吵起来。过了一会,某个电话被写在门上的社区的人过来了,物业的人给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趁机走出去了。
这个时候其实周围已经聚集了一些人,大家都在说怎么回事,我出去的时候还有人在那 喊「小姑娘进来哦,不要出去,不要出去」。我在门口立刻就开始打车回家,我特别害怕在我车到之前警察过来把我强行留下——确实也是我报警的。我打的车过来的时候,有一些自发的红卫兵,在门里面开始拿着手机对我录像、录那个车牌号,跟司机说,「你不要载她!这个小区现在被封控了」,非常恶心。很无语的是有一个女生,她刚进去小区五分钟,所以她说服保安让她出来了。结果她自己出来后,跟我说,「小姐姐要不还是回去吧,要不会坐牢的」,她还是以一种善意提醒的方式跟我说,就很无语。
还好那个司机人很好,没管他们。我在车上的时候就接到警察的座机跟手机的电话,我也开始给他念法条。我一边念法条一边用常人情理来说服他,我说我每天上班,两点一线,我知道我不可能感染,我也每天做核酸——其实我没有每天做——我说我完全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没有空做别的事,我现在跟你承诺我立刻打车去核酸点做一个核酸,接下来一周我都在家里面,每天也去做核酸。
反正扯了很久,我那天打车去做了核酸——其实那段时间我已经很久没做核酸了——做了核酸我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我确实也在担心,他会不会又来找我之类的。我回家之后给他发了好长的一个短信,编瞎话试图感化他。
我就说,跟你说一下我今天为什么态度那么着急,那么急着走,我怀孕了,才两个月,这是我们家第一个孩子。我还编了一些细节——我说我有多囊卵巢,你可以查一下这个病是很难怀孕的,我们尝试了很久,我每天要回家吃补药,周末还要去产检什么的,我不可能留在那,我不知道这个封控有多久 ,我们都是老百姓能不能互相理解一下。
我还补了一条,说我会算命的朋友看过了,人家说三个月之前最好都不要跟任何人讲,等稳定了再告诉别人这个消息,我今天跟你解释这个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情况,大家互相理解一下。这是我们家第一个小孩,现在国家号召大家三胎,我也不希望因为今天这些小的纷争,影响我们家这个小孩,到时候如果真的小孩没了,我也是会要追究责任的。他可能真的被我说烦了,他就说,反正你要记得给你们小区报备。
后面也没有人再来找过我。
后来我把那个截图发到群里,我有朋友真的信了,以为我真的怀孕了,问我什么时候怀孕的。
(笑)
虽然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利用了女性身份的一些东西,可能也利用了警察「这个女的好麻烦」这种潜意识的心理,但是,好吧,反正我有子宫,我利用一下又怎么样呢?
这一次封控结束再出门的时候,有什么印象吗?
我记得那一天大家出来吃饭,就感觉还挺…还挺…有一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吧。
末日狂欢
2020年第一次被(国保)找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当时因为没有经验,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很恐惧…很难受的吧,就是我不想在这儿 跟你们说话,但是又不可能站起来就走。
(沉默)
第一次被找是直接有人敲门。有一段时间我听到有人敲门——甚至我现在很多时候听到敲门——都会很难受,生理上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后面再被找的时候,就越来越生气,觉得你们就是在骚扰我,所以我到最后被找,会直接当场跟他们说——我觉得你们就跟偷窥狂一样,你们自己工作有意义吗?你不觉得你老了之后会遭到报应吗?你老了之后会不会后悔?会直接地让他们意识到,我看不起你,在这儿跟你说话浪费我的时间。
他们意识到我的不屑之后就说,「不瞒你讲,我们也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就开始阐述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就会说oh really?开始阴阳怪气,「你说的太好了,你被教的这些话说的好流利,非常好」。
他说,「你不要在这儿逞口舌之利」,我说「谢谢你的自我介绍」。
没有一句话想跟他们好好说。
他们也会一会儿扮好人,一会儿扮恶人,暗示你他们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最开始确实没有经验,也确实比较恐惧。虽然我觉得我第一次的时候,已经非常努力地在夺回主场。当时我听到一个警官跟他女儿打电话,我就开启话题说,「我是在做儿童青少年性教育,你有没有给你女儿做性教育啊?我给你推荐一些做儿童性教育的公众号吧?」我后来意识到,我当时是非常努力地想要夺回一些话语权,其实我也不想跟他们聊任何的话题。
我给他看了一些性教育的公众号,他就说这个内容还挺好的,你们要是做这些事,我们也不会来找你。我说我就是做这些事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找我。我当时还跟他们聊说,如果你们以后的小孩是同性恋怎么办?尝试发起一些我这边的话题,有女儿的这个反而态度还可以,我忘记了具体的对话,他的态度就是,如果她真的是同性恋,那我也没有办法,类似这种回答。反而是那个跟我年纪更相仿、还没有结婚的年轻警察说,「怎么可能呢?我儿子肯定跟我一样喜欢女的」。 他没有结婚,就觉得自己肯定会生儿子,然后儿子肯定是个异性恋。
(笑)
跟那个有女儿的父亲进行这样的对话,是什么感觉呢?
是很复杂呀…你会感觉到,他也是人呢,居然。
他居然也是一个父亲呢。
但是你同时又知道,他就是一个机器的一环。以及后来发现他连word都不会用,他不小心把那个word按起来,那个时候笔录快做完了,他就很惊慌,「哎呀我的页码怎么没有了」,你就发现这个人连基本的办公软件都不会用。
你可以看到他的很多面,会觉得特别可笑。
去年年底乌鲁木齐大火,以及之后发生的白纸运动,你对那个有什么印象吗?
白纸运动的时候,我在的城市也有上街,我当时有想要不要去。但是因为我十月十一月刚被找了,大家会提醒我,还是不要去了。我自己也在想,我刚被找了没几天,如果我又去的话,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进行什么追踪。我没去,但是那几天特别焦虑,因为你会不停地看到很多抗议现场的视频和照片,感受也很复杂——哇,中国人还能这样呢,完全没有想到。另外一层就觉得,天哪,太苦了,我们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刻才敢做这些反抗?已经被压了三年了。
然后也很担心——我已经知道了做很多事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也付出过一些代价,你会担心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收场,也会知道明天可能就看不到了,我把它存下来。既然不能去的话,至少我把内容存下来。进入了一个有点应激、情感很封闭的状态,我以为我看到那些照片,我会哭或者会怎么样,但其实没有任何情感反应——最重要的是把它存下来,就是不停地在刷,不停地在存。
我爸那天刚好又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一个「大国抗疫」之类的东西,就直接撞到枪口上了,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开始怼了几句,情绪挺激动的,他又开始他的中庸发言,说「你要理解」什么的。我特别生气,你要我理解什么?
我就开始发疯,开始不断罗列那些不用认真去回忆,就能想到的事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我,宠物被当面弄死的可能是我,家里没有吃的的人可能是我,生病吃不上药的人可能是我,我说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你叫我理解什么?我理解什么?我已经活不下去了,我理解什么?
我越说越生气,就开始攻击他,我说你也在搞什么疫情防控,你觉得有意义吗?你觉得你在为人民服务吗?你不过就是给领导捧臭脚而已。之前我爸妈他们被找了之后,他们会让我主动加那些警察的微信,说他们要见我,我爸给我推了两次警察的微信,我就被trigger了这个事情。我这几年已经反思了无数次,反思我哪里做错了,我有什么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没有任何问题,我说也该是你来反思一下,我们的父女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之前跟我爸的关系还可以吧,就是这三年…其实跟我爸发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反而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好像达到了某一个顶点,一直在哭一直在哭。跟他发完这疯之后,我自己又哭了好长一会儿,都忘记了…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吧。
我当时还分化出另外一个自己,说我要记住一下我现在哭了哪三个点…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具体是哪三个了 。
一个是觉得这些人太坏了——所谓这些公权力、这些颁布政策的人,这些人太坏了。另外一个是像那句话,「可是心很痛啊」。
这句话是韩国当时学生运动,有人问,你们其实知道做这件事,很大可能会死掉,为什么还要做? 有个受访者,我忘记具体的语境了,但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可是心很痛啊」。
你还是会要想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承受那种心痛的感觉。
(沉默)
后来意识到我有一个自己的issue,这是我和我的咨询师的沟通当中,唯一一次哭——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一个所谓导师一样的人,我一直会很期待有一个,在我关注的很多领域上,走在我更前面的人。当我很沮丧的时候,她可能会跟我说,「没有关系,都会过去的」,因为她已经可能经历过这些了,所以你会相信她。我看到一些朋友在读博,有时候会分享一些跟自己导师的互动,就会很羡慕。
因为我会觉得很多时候,尤其在那种沮丧和失望的时刻,如果有一个你信任她的、好像已经走在更前面一点的人,跟你说没有关系,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我好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是有期待这样一个人的存在的。但是可能这个人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可能你得去做你自己的那个人。
(沉默)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宣布防疫政策彻底结束了吗?
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时间,好像突然有一天就结束了。
当时感觉非常荒唐吧,我记得网上还有那种视频,工作人员开始撕掉地铁口的那个健康码。哇——完全没有预料到。
解封后没多久我自己也感染了,没有一线城市那么快。可能晚了半个星期到一个星期,那段时间特别虚弱特别痛苦。
什么时候好起来的?
它的病程比我想象的长,至少有两周吧。第一天第二天发烧的时候,真的非常痛苦,蛮久没发过烧了,感觉好虚弱,发烧发得我都感觉要死了。前几天甚至是吃不下东西的,有那种恶心或者拉肚子的一些症状。中间有一天好了,发现我可以吃东西了,就特别高兴,但后面又开始烧,烧了差不多有一周。
第二周就是没有味觉、没有嗅觉,那时点了一个豆汤饭,我想应该很香吧。点来之后什么也闻不到,我就想是这个豆汤饭没做好吗? 外卖附赠了辣的小菜,我把小菜打开来闻了一下,发现什么都闻不到,那些以前觉得好吃的东西,现在吃到嘴巴里味道很怪。
差不多持续有一周左右,加起来一共有两周吧,比我想象中要长。恢复过来之后立刻出去玩了,去见了很多朋友。
你还会跟朋友聊起疫情期间的这些事情吗?
很少吧,大家都不太聊起过去的事情,不会有人特别主动地聊。大家不聊并不是说大家回避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大家回避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很创伤。
昨天好像因为什么聊起来,我当时都没有说太多话,是朋友们在说。我听的时候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就是立刻堵起来了,胸腔到腹腔的这一块堵起来了,那种感觉。每一个人都特别创伤,不管这个创伤是来自跟家里人吵这些疫情相关的事情,是所有那些让人不能呼吸的管控,还是这些管控产生的社会的问题,一提到就很难受。
19年的时候,你对自己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其实19年我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我回国之后有去医院看医生。但是你肯定不可能想象到,未来三年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
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所谓的好事,当时我的一个作业还投了一个联合国妇女署在泛亚洲地区的一个会议还是什么的,被选中了,当时要去做分享。其实我已经开始办签证、订住宿,钱都交了,突然收到一个邮件说,因为一些不可预见的原因,暂时不做这个活动了,当时外媒肯定是比国内的媒体更早意识到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
昨天大家讲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当时她在日本上班,在看电视,好好地突然出现一个警报说明,说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病毒,已经从武汉传染到日本了,必须引起重视。这种警报一般是日本每一次有大地震之前,所有电视台会立刻跳出来的。我朋友现在回想到这个时刻,当时中文媒体没有人承认这件事情,她在那边的中国同事大家也觉得肯定是外媒对中国的抹黑。
最早选择学性别研究这个专业,是想做学术,还是想做相关的公益之类的?
其实我当时学性别研究这个专业是抱着一种「我要回到我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来做事」的心情——并不是所谓「报国」的心态,只是会觉得这些知识,我很想要把它用到我生活和感受的这个环境里来。没有想过一定要做学术。
所以19年的时候还是想着回到这里做事,那其实你之后几年确实是一直在做你当时想做的事情。
之前其实也有做一些事情,参演过《阴道之道》的话剧,后来也一直在做性教育。其实留学的时候有想过,在我读书的城市演一场《阴道之道》,我们当时也组了一个群,如果第二年回来肯定是要做这个事情。
那你现在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我今年就非常明确地觉得…嗯…就觉得要离开。
(苦笑)
就是要离开,再也忍受不了了,各个方面。今年其实有想继续读书,但是我不想读PhD,我想做的很多事它不是纯理论的。如果我要读书的话,我肯定就是只能读性别相关的专业。但我并不觉得性别相关的事情,它是靠读书可以去…它肯定会有成果,但还是会给我一种在象牙塔里的感觉,我可能还是会想要实操性或者实践性更强的一些…所以如果要读,我会想去读社工吧,这几年也参与了很多助人的工作坊/课程,也有一定程度地介入一些个案。我就会觉得,我还是蛮愿意、也蛮擅长做这些事情的。
其实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我很适合去读律师。因为吵了很多的架。(笑)我能感觉到我的辩论能力、观点总结、反应能力是得到了很多的锻炼,但是总的来讲只是技术而已,它没有真的触动到我的内心或者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让人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它不会让我感觉到真的有成长。
所以对于你来说,助人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是的。
你有想过,如果离开了,在另一个土地、环境或者社会里,做助人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感觉会和你在这里一样吗?
我觉得肯定还是会不太一样吧, 就是假设我真的去国外读了社工,在社工的那一套培训体系里,我也要去考一些证 、也要积累时长、可能也会有很多工作会给你带来不适的感觉、可能也会有语言文化信仰各方面的不同。
就是可能,它也是一个需要吃屎的过程,只是我不想在这里吃屎了。
(大笑)
你说的离开是永远地离开吗?移民?
对,我会把它当成一个比较长期的目标。
因为我感觉我在这边——尤其跟朋友们在一起,虽然好像这种生活已经过了快一年了,但是依然有一种末日狂欢的感觉。接下来50年不可能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可能永远这么安全、所有人都在。
在这个地方除了所谓的吃喝玩乐之外,大家不可能还能做更多的事情。
你已经不相信这个地方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了?
不能说不相信吧,我会觉得对我来讲已经到一个临界点了。
你从2020年到2022年确实经历了很多事,最早几次他们刚找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呢?现在是会觉得自己的处境更危险了吗?
嗯…他们对你持续的监控和威胁,确实会造成很多自我怀疑。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我的微信是被看着的,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看、在哪些节点会看,很多时候我的自我怀疑就是…比如我分享了一篇文章,过了三分钟就没了,我就想,难道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反向监测哪些文章该删的渠道?就会有这种影响,有时候看到一些文章就想,我到底转不转呢?我会告诉自己说哪怕就是因为我被删的,也不算我的错。
但你就会这样联想,在那种自我审查最严重的时候,我会去想一些非常糟糕的状况,基本上有两个状况——一个状况是自杀,另外一个状况是被关起来了。我有想过这两个状况,自己是不是都可以接受?我想了一下说,可能都可以接受。假设有一天我没有办法忍受的话,至少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我最后保留自主权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很坏的想法是,那有没有可能所谓失去自由?想说也可以接受吧,因为我感觉假设我真的进去了,我可能还是会尝试做一些事情,在监狱里面还是可以做一些事的。
我知道我去设想这些状况,是我的精神肯定是受到了一些 …到了某一个极点。但是确实想完这些,我发现在我的想象当中,失去自由或者失去生命这两种情况,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可能真的到了具体的状况下又不一样,但至少在我的设想中是可以接受的,这都无所谓的话,还有什么特别有所谓的事情呢?
去想象这些状况其实就是一种应激,一种被破坏的结果,就是一种创伤。
但是,想象一下的话,也可以吧。
你觉得这三年对你来说,结束了吗?
我觉得没有结束吧,我觉得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结束。对有良心的中国人来讲,就不会结束。可能程度不一样吧,比如你真的在方舱经历了特别糟糕的生活环境和对待,可能会真的产生很多躯体化的反应,对普遍的大众来讲这种精神上的压力,是很难很快地消除的。
它是一个集体性的创伤,你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一个具体的人,真的就感觉是一种集体创伤。
你觉得还有愈合的可能性吗?如果有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形式?
我觉得愈合,怎么定义呢…我觉得它可能会有机会,不只是创伤而已,可能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缝隙去变成其他的作品、其他表达的。
我有一个朋友,她的专业会有一些创作的课程,她也会写一些小说去比赛。我给她讲过 我在疫情期间的故事,她后来把一些事情写到了她的小说里面。那个小说被现场点评的时候,有很多男老师不喜欢,非常直接地说不喜欢,但是也给不出很好的理由。但是现场有一个女性评委,也非常直接地说,这是20篇小说里面她最喜欢的一篇。
那些男评委好像有一种「现在的年轻人经历的这些事算什么?」的傲慢——你写的这些细微的小事,有什么好记录的呢?你好像对这个世界很不满,但是你看你的处理方式?他们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优越感吧。那个女老师就直接在现场说,她写这个小说就是在处理这种不满,对于这个作者来讲,她可能已经没有其他的空间来安置发生的这些事情了,所以她要把它写成她的小说。
对于你来说你的方式是什么?
我的方式…可能现在还没有把我的经历变成什么其他的东西。假设我要写小说的话,可能是50-60岁?反正不是一个当下的任务。
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跟朋友讲述吧,大家一起聊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疗愈效果吧。
对你来说这整个三年,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或者对于你来说,浓缩你对这三年的 印象或者记忆的某一个时刻是什么?
我刚刚想说装怀孕的那件事,因为我觉得太好笑了。
但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其实去年年末大家上街的那几天,我是有一些朋友去了。大家在现场确实是有很多担忧的,当时有个朋友的书包,有点像那种户外包,有很多小带子可以挂东西,大家就每个人抓住包上的一个小带子,怕被冲散了。有一张这样的照片,那天晚上大家在人群中,大家都有一点害怕,大家都抓住了这个朋友的书包。这两天这个背书包的朋友也要离开了,就有朋友送了她一个版画,那个版画画的就是当时所有人伸手在一起的这个瞬间。
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完全能够感受到那种感觉吧,会让我想到一段话,也是一个朋友写的或者摘抄的:
能帮助洪流之中的人抵抗浪潮的,其实始终是爱,真切而具体的爱。
爱一个具体的人,因此希望她远离不公与苦难,自由呼吸,生活生长;爱一座城市,因此希望它始终光辉灿烂,不会堕入强权的泥沼;爱这座城市里每天擦肩而过的人,因此希望他们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爱自己,因此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同样的自由。
爱本身就是革命,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得爱的能力,获得分辨爱和斯德哥尔摩症的能力,以及获得不爱的权利。
大家最后都安全回家了吗?
都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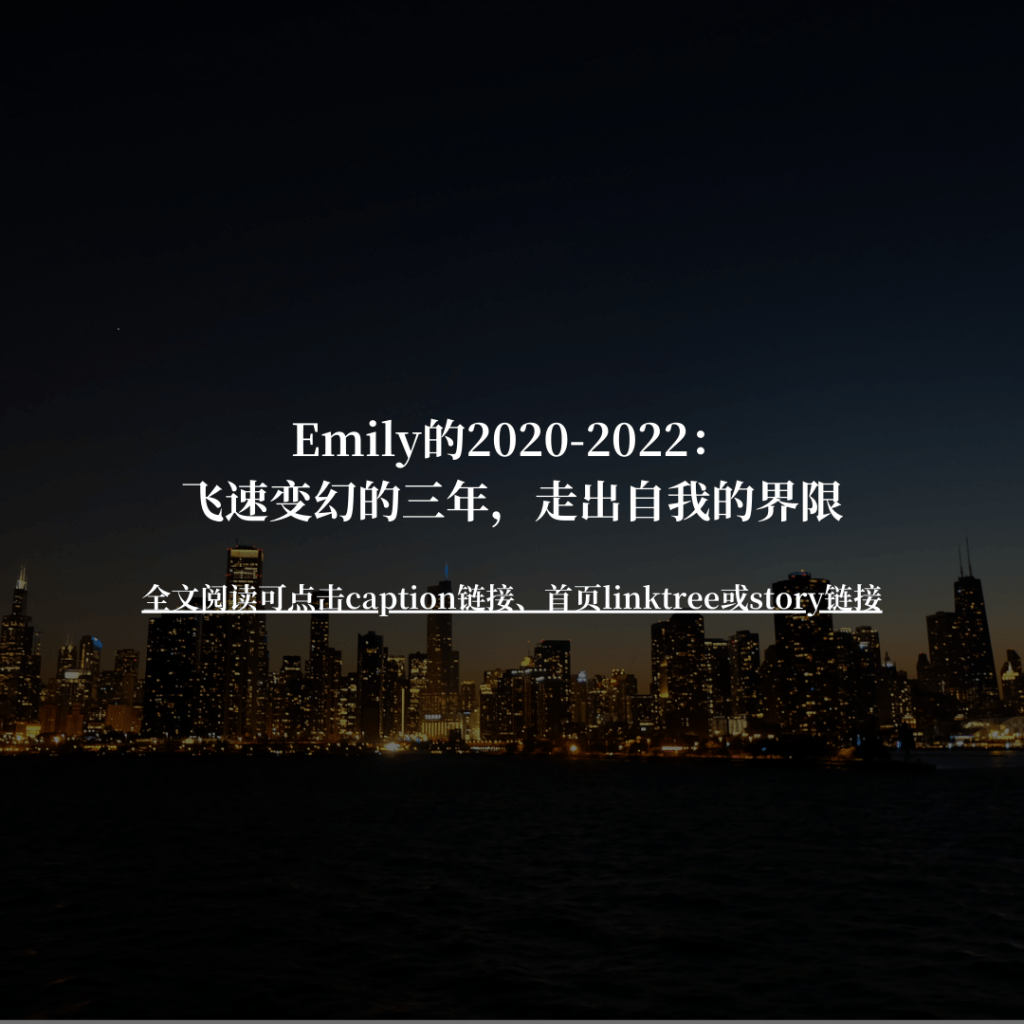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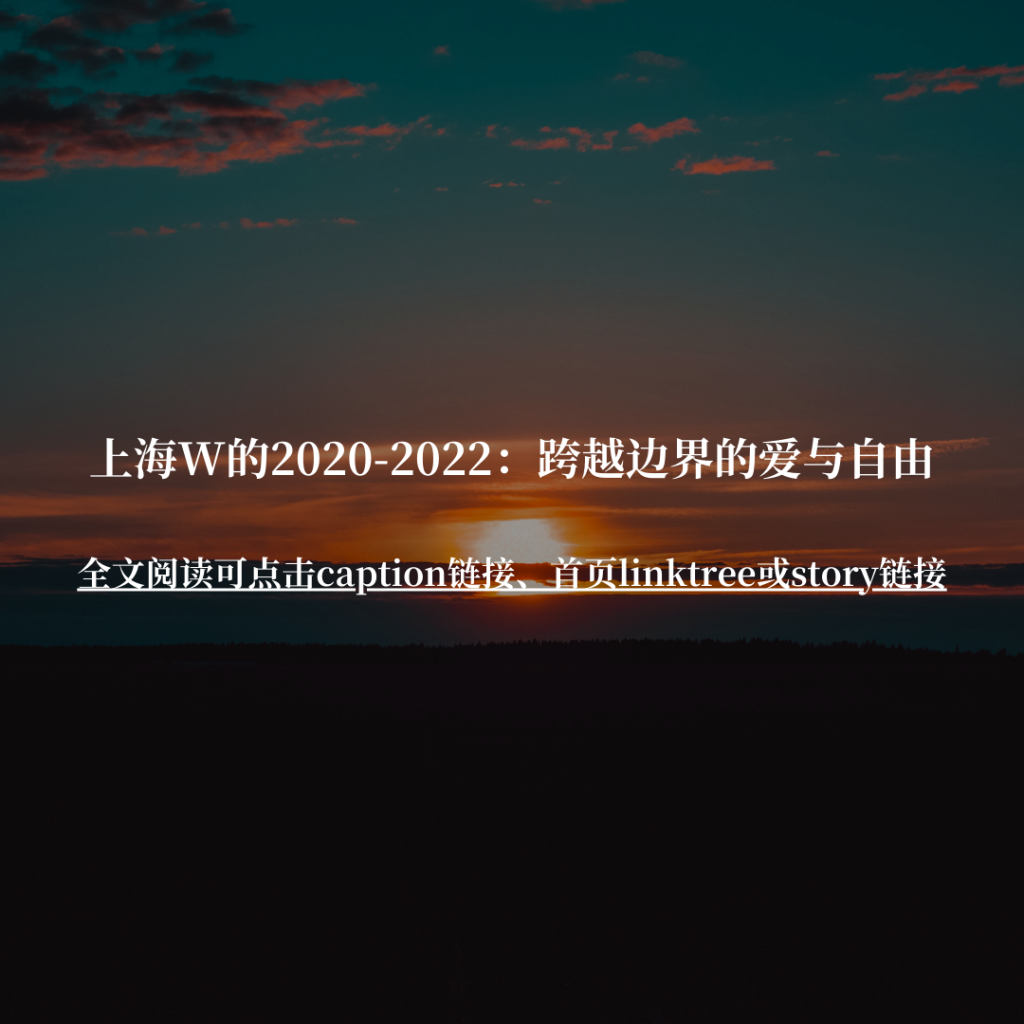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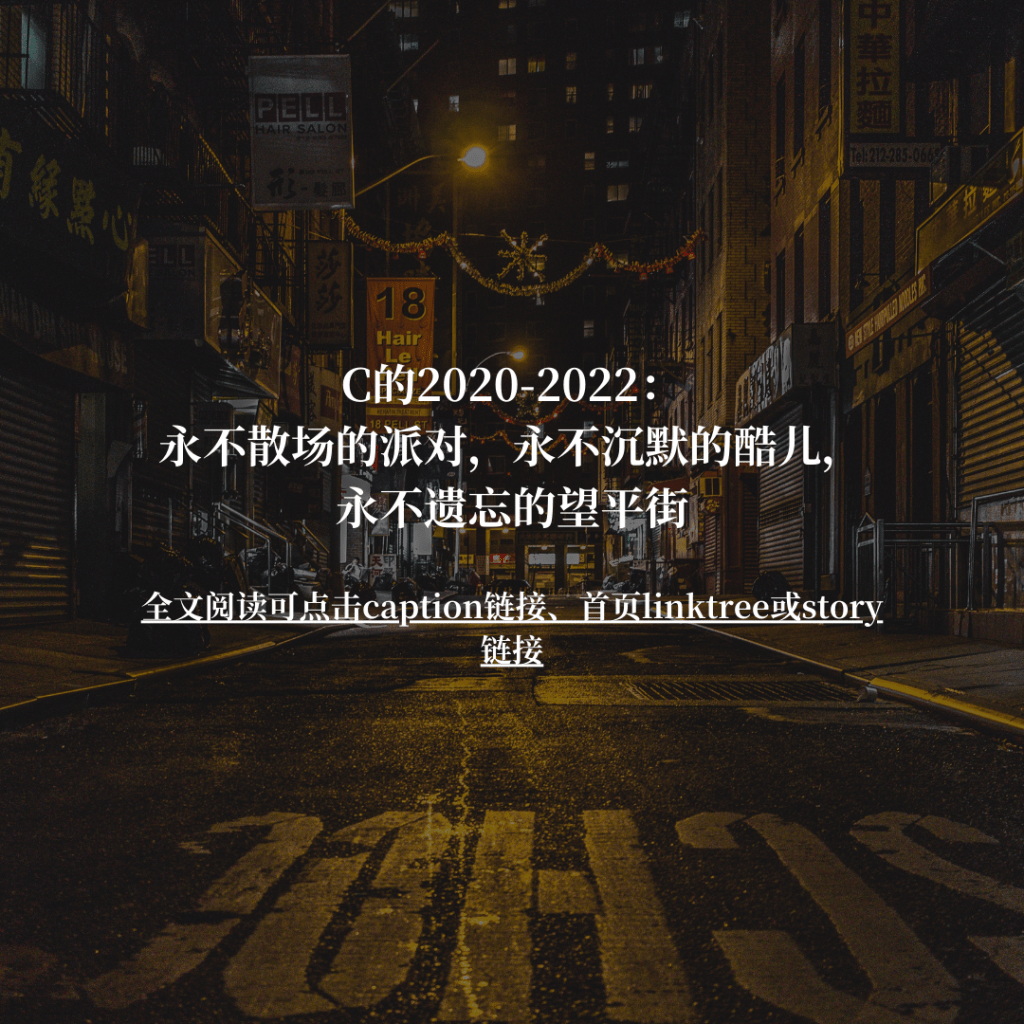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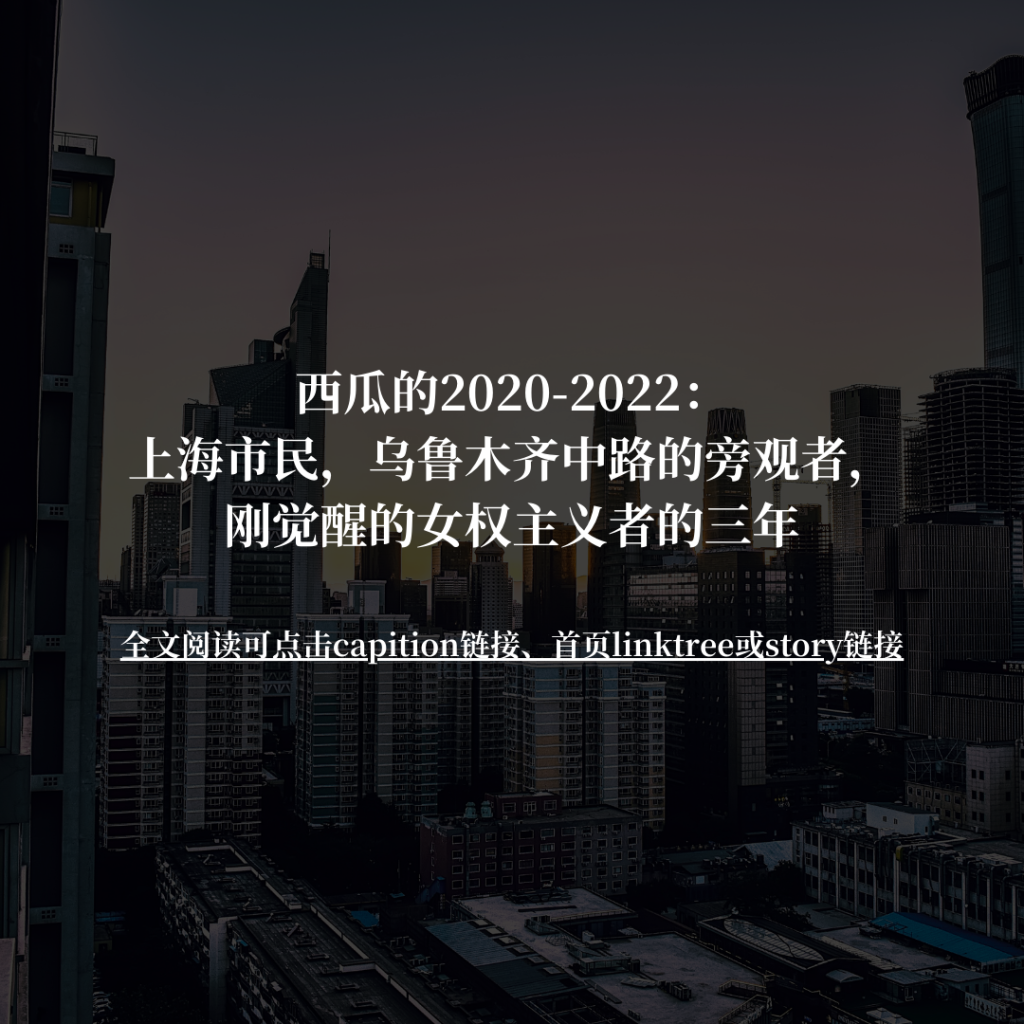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