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W
职业:学生
标签:脱中者
年龄:00后
性别:女性
2020-2022所在地:上海
生活地区:日本
访谈时长:140分钟
访谈时间:2023年12月19日
访谈人:小A
校对:Chris
关键词:上海封城;艺术;方舱;留学;酷儿;
PART I
逃离上海
其实19年的时候就想来日本(留学),但是正好那个时候——20年初的时候——已经是疫情嘛,日本没有开国门,我就没有办法来。后面我就一直在国内上一些课、打打工啊、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尤其是20年——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还是可以出门的,但是大家都不敢出门。
疫情刚刚有风声出来的时候——特别是看到李文亮医生的事件,我就紧急在网上买了很多口罩,还买了消毒的东西。当时我和我妈留在上海,我妈还不信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干嘛买这么多口罩。但真的没有想到,没几天疫情就全面爆发,整个国家彻底乱掉。我们那时候也不敢出门,如果要倒垃圾什么的都会穿得很严实,自我防护意识很强,但是反而没有像之后那样管得这么严。
不过比去年封城的时候要害怕很多,因为一开始它主要还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就是很害怕病毒这个东西本身。因为那时候是真的会死人,所以说肯定跟去年没法比。
你对20年疫情爆发的一个最早的印象是什么,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瞬间,让你意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或者发生了?
我应该是受互联网的影响吧,觉得大家都在说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你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可家里人或长辈不把这个当回事。还有就是在疫情的初期,我们作为民众什么都做不了,但你看到互联网上这么多在武汉那边的医护人员、或者一些在做志愿者的朋友们——他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我当时看到很多医护人员,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而在微博上发求助视频、哭的视频。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看这些东西,每天都看上海新增、武汉新增,发现一天比一天严重,非常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的是很多人会觉得它没有事关自己的利益,所以不要紧——比如我在家庭群说这件事情,他们都觉得我在大题小做;大年三十除夕夜的时候,他们上头还在举行什么春晚、歌舞升平,就是不关心真正的受灾地区、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是很难过的。
当时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吗?而且你还在计划去日本?
2020年3月份我过生日还被封在家里,但是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出门了。日本在2020年年底开放了一波,但是我家里人觉得不着急,我就没有赶上那一波。(21年)1月份又开放了一波,我也没有赶上,就一直到了2022年才来的日本。
那个时候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日本的求救视频,很多医院你打电话,他们是不收你的,没有医院收新冠患者,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2020年封城的时候,你们家里的日常生活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当时买了很多消毒的东西,光是口罩就买了一百个。我们家里有四个人,每天都在省着物资,当时我和我妈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尽量是省着用口罩。但是买菜什么的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只不过不可能随便叫外卖,因为当时经济已经瘫痪了,大家都不工作什么的。
日常的一些基本需求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但我觉得精神上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
当时就是无助。不只是因为不能出国,每天跟家人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很压抑——因为我说的话没有人愿意听,家里人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要暂时待在家里而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那些在求救的、因为新冠死去的人们,包括李文亮医生,最后他自己都没有得救,他也走了,我觉得是很心痛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比起自己,我更关注的是武汉那边在求救的人、或者得不到医治的人。
当时和家里人聊这些东西吗?
会聊,但是没有用。他们的反应会让我觉得心灰意冷——怎么会是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会(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明明大家是共同体,你们却只在乎自己。我觉得我家里人是在用着一种很特权的…因为他们做生意,觉得(收入不受影响就)没有关系,但是没有看到那些生病的人们可能经济上没那么好。看到家里人站在高处,没有办法去共情那些在困境里面的人,这会让我很难过。
你觉得这种情况在22年上海封城的时候有改变吗?
我觉得22年是跟20年截然不同的状况。
我当时是已经准备走了。3月份我刚好网课结束,(去日本的)机票是订在5月份,原本计划休息一两个月玩一玩就过去。
那个时候上海已经陆续有人感染,已经有风声说会封城了。
我是生日那天拿到的签证,拿到签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我问保安,“是不是今晚会封。” 他说不知道,让我先回去,结果当天半夜我们小区就被封掉了。
那个保安其实是知道的,他眼神很躲闪,但我当时没有想太多——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事,当时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糟糕,从3月中旬我拿到签证那一天,封到了29号。
当时我身边也有朋友准备来日本,他们(3月底)一解封就订机票,连夜理好行李,去机场马上走,就是他们刚好在封完第一波、开启第二波之前的那几个小时、那一两天里赶紧走了。他们很聪明,直接跑掉了,但我没有走。
当时有个消息出来,浦东封三天,浦西封三天,我朋友趁那个间隙赶紧去机场了。
我当时真的以为会解封的,但是没有想到一封就是三个月,我想着一个月差不多得了吧,不能再久了,再久人会疯掉。封城期间他们不是会每天开发布会吗,我一直都有关注,但(他们)每天都讲一些没有用的屁话。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是,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骂上海人,说你们不乱玩就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封城期间,不知道你们自己家里有物资困难的情况吗?
没有太缺。可能是因为我妈妈有认识的人,会给她送过来。而且我们家人不多,其实每天吃的也不是很多,吃这方面还可以。但是居委会送的菜是挺少的,要是我们家没有别人的资助的话,肯定是不够的。
我记得一个领导要来我们这个区,我们徐汇区所有家门上的封条一夜之间都被拿下来了,就因为那个领导来我们区。后面他们又要贴封条,敢贴我们普通民众的家,但不敢贴领导那一块——法租界那一块,他不敢贴,从来不贴的。
我觉得挺搞笑的。
我有基础疾病,本来是定期要看病,每个月去医院打针,当时也去不了,叫救护车——前面可能排了500多个人,我叫不到。就算我能找到机会去医院,我原先去的那个医院停止治疗了,他们说有另外一个医院(可以打针),但是离我家很远很远——就是我可以去,但是(去了)可能回不来,没有车送我回来,我可能就要被关在那边。我就觉得算了,不治疗吧。因为打针嘛,我不能在家自己打,另一方面我还要吃药,药家里是有的,但是我当时阳了,我和医生沟通过,他跟我说不要吃药,我就是小半年没有吃药,以至于后面我这个病是有点不太好 。
这三年,我觉得他们是在自欺欺人——就是经济真的很差了,上海的外企都已经撤离了,人民币一直在贬值。我自己做艺术类,如果要做社会问题,在国内怎么做——还是出来比较好一点。
在经受了两个月的封城这种很压抑的情况后,我精神确实有一点出问题了。我那时候正好跟前任分手,状态很差,整天在家里面。我们家当时防护做得很好,因为我怕被感染走不成,结果订了5月份的机票还是没走成。上海当时有个通行证,你可以靠这个通行证去机场——就是你要去国际机场的话,车上必须要有通行证,应该是有权力的人才可以拿到那个通行证。当时我们是听说有这个东西,但是最后也没找到关系。
4月下旬的时候,我妹妹感染了。当时每天要做核酸,早上很早的时候去门口排队做核酸。那时候我们在家里会做很严格的防护,但反而是因为医护人员疏忽了(感染了)——他没有做好消毒。我妹妹跟我讲,她看到那个医护人员刚做完上一个人的核酸,都没有消毒,就直接给我妹妹做了。她的手碰到了我妹妹的口腔里面,我妹妹第二天就发烧了,就感染(新冠了)。 她那个时候可能是弱阳,我们每天都在很好地消毒,算好了她使用厕所的时间,除了上厕所不让她出房间门, 然后我和我妈妈一起睡。为了能保证我顺利飞走,全家人牺牲蛮大的。
我妹妹感染之后在家里呆了几天,但是小区可能有政策不允许,最后就还是被送去方舱了。
妹妹是07年的,15岁。我妹妹说方舱条件真的很差,全天开着灯,几百个人在很大的一个场子里面待着。厕所很脏,没办法上厕所——上面全都是排泄物,很恶心。说实话,在那样的场所隔离,有些人可能本来没有被感染,被送进去后反而直接被感染,因为在里面没有防护措施。
我妹妹被送去方舱之后,我和我妈在家里待着——只要我跟我妈保持核酸阴性,我就可以走了。但是我妈有一天突然被打电话说她阳了,然后我妈也被送去方舱了。我妹妹在里面待了6-7天,我妈妈待了4天出来。但我妈妈之前每天都是阴性,她其实没有阳,是报告错误的假阳性。她是在方舱里面阳的——她回来之后那几天很不舒服,一直低烧,她以为是着凉。那几天我们一直待在一块儿,也不知道她阳了,我当时可能也被她感染了。
后来她又被送去方舱,我跟我妹妹也被告知要被送去酒店。
当时算上我跟我妹妹,我们街道一共有八个人,其中一个阿姨还抱着婴儿,穿着防护服去隔离。他们刚开始说要把我们送去酒店,但其实把我们送到一个像是集装箱的地方——在学校里建的,有很多集装箱的地方——我们到了之后全都傻了。他让我们签字,我当时就说我不签,也跟我妹妹说你不要签,我们谁也不要签。当时还有一个中年阿姨,她说我们所有女的都拒绝签字。
当然我也是很体谅医护人员的——那个时候真的很晚,10点11点了——医护人员全是女的,可能就一两个男的,她们就跟我们一起调解这件事情。我知道她们也很为难,但我说我们今晚一定不能签这个字,签了之后进去肯定就出不来了——我们不相信上头、不相信任何组织(的承诺)。当时我们跟她们吵了两个小时,真的是吵架,然后我跟我妈妈打电话说本来应该是去酒店,怎么被送到这个地方来。 而且我有基础疾病,我不能去这种地方,我身体肯定会更不好。我妈就给居委会打电话问怎么会这样——因为她跟居委会关系还不错,居委会他们也打电话说帮我确认。我们闹了两个小时,他们最后把我们送到酒店——在我们的一个…也算是抗议下,把我们送去了酒店。
我们出来上大巴去酒店时,看到另外一圈大巴过来——他们可能听到了我们抗议,就没有开进来,而是把人直接放在学校门口,让他们自己进去。他们可能也怕这些人像我们一样抗议,然后再跑掉。我们当时幸运,因为有个阿姨带着女婴,可能这一点帮到了我们——那几个医护人员也挺好的,他们觉得这样(的隔离环境)确实很不好,毕竟还有小孩。当然我觉得整件事情都不对,不应该有封锁,我们当时除了比较幸运,也比较敢吵敢骂,给各种机构打电话。
后来他们把我们送去了一个五星级酒店,进酒店当晚我就发烧了,立马跟他们打电话要求把我跟我妹妹分房,我不希望我妹妹再感染。接下来就是比较压抑的几天,不仅要看着网上很多人骂上海——我当时还因为这件事跟网友吵架——而且自己又在发烧。
当时他们说你要保证多少天非阳性,你才能出去。我刚进去的时候一直没测——当时那个测核酸的阿姨人挺好的,她跟我说先不要测,等几天看看能不能自己转好,就可以回去了。但是第八天的时候她说必须要测了,几个人进来给我捅鼻子。由于我当时有基础疾病,那几天她还会给我送中药,但我都扔掉了,我不想吃中药。
后面因为我阳了,又有基础疾病,我强烈跟她要求去医院,就被送到了定点医院。但那个医院我觉得也很不人道,三个病人一间房,三个人都是阳性,我在医院又待了两三天,转阴后他们就让我走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我到了小区门口还跟居委会吵了一架。因为我当时是带了电脑和护照一起去隔离的,我想隔离结束后,看能不能找机会直接去机场。回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他们要求我把所有东西拿出来,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狂喷消毒水消杀。我说这怎么可以,我的iPad、我的一些纸质的文件全在里面,你怎么可以给我消毒,你这样做对吗?这些人就是没有一点医学常识,我当时跟他在门口吵了快两个小时。后来我就说,你把你们领导给我喊出来。另外一个居委会的两个男人就出来了,他说,你能不能好好讲话。我说我不能——今天你要是把我东西拿去消杀,我就在这不走,你们自己看着办。当时可以在小区里自由活动,所有人都出来看我。我们小区里老年人比较多,他们都不敢吵架。我是已经跟居委会吵过好几次了——但他们这次也不敢继续跟我吵了,(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可能怕别人也学我一样出来吵架 。
他们本来说那些东西要放7天还是14天才能拿回来,我说不行,最后协调到半个小时——他说半个小时消完毒后亲手送到我家门口来。我走进小区的时候,还有一个医护人员一直跟在我后面消杀,反正就是很没有意义。
那个时候好像是5月末了,我订了6月份的机票。其实6月4号就已经解封了,但是我解封的时候也没有出去玩,因为我怕还有病毒在体内。因为我要出国,日本海关要求的核酸的格式也是不一样的,医院可以开证明,但是我不敢去,因为太多人了,我怕又出什么事情不好解释。后面我找了一家在浦东的私人医院,做一份核酸大概是400多。
做核酸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找公立医院呢?
公立机构的正常渠道60块一次(核酸),但是我不敢找公立医院。
首先是他们的格式可能会有误差。第二点是,像我这样的阳过了的情况,公立医院如果觉得核酸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忙到没有时间听你解释、看你提供的这个证明——他们可能就再把你抓起来了。所以我觉得钱花就花吧,真的没有办法,这个过程挺恐怖的——我再也不要经历这种事情了。
我飞的前两天就做了,(但是)航班当天中午都没有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很慌了,让家里人开车送我过去现场看这个结果。等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他跟我说核酸有问题,我当时一下就哭了——核酸有问题,我不会又走不了吧? 国内跟海外的标准的CT值是不一样的——国外可能34、35就已经算阴性了,但国内的标准是38 。医院这边就可能是按照原来(国内)的CT值来算,可能我身体里面还有病毒,还算是阳性。
我当时都激动到跟我妈打电话出柜的程度了——当时也是脑抽了,直接跟他们出柜了,就觉得要是真的走不了就一了百了,要死一起死吧。当时已经下午3、4点了,我机票是晚上7点的,从医院过去还要40多分钟。
后面我跟那个私人医院说,我忘了和你们说,我之前进过医院,当时感染过,去过定点医院。他们说你要早点讲,如果不讲的话就会算我核酸有问题,算我阳了。我跟他们讲了之后,给了他们我在医院隔离的证明,他们才说你核酸没有问题,可以走了。因为如果你是才阳的话,这个检测值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你阳过,这个核酸就说明那个时候你病毒很弱了,说明你没有什么传染性,是比较安全的。
当时是我舅舅送我去的医院,我妈让我不要告诉他我的核酸阳了,因为她怕我舅舅不送我。我是飞机起飞check-in前不到两个小时才拿到核酸报告的,当时开车40分钟赶过去,还好赶上了登机。
我当时从香港转机飞东京,到香港之后我就已经释放了,整个人已经没有压力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新冠是真正结束了。
其实我虽然个人的政治立场比较激进,但之前也只是准备出国(留学),完全没有想过要留在日本。但是这三年经过毒打,我觉得一定要留在国外,我再也不要回去了。
没什么好回的。(笑)
PART II
CHOSEN FAMILY
去年上海解封之后,陆续很多其他城市也开始封锁。再到去年的乌鲁木齐事件——我觉得真的是很恐怖、也很痛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那件事情,说实话到现在中国可能还是一个处于动态清零的状况,可能还没有解封。
我记得当时上海的话——我可以在你们这边说吗,应该没有关系吧?
我记得当时是乌鲁木齐他们率先开始游行,然后上海成都等各大城市开始响应。去年上海游行我朋友也去了,他们差点被抓,但是他们逃了。我后面记得我的情侣朋友,一男一女,那个男的先被请去喝茶了,他为了保护女友,一直装死装不知道,装作没有参加过这个游行,就导致他被多关了好几个小时,后面没办法,还是讲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要为对象好,导致被多关了一天。很多人被抓——他们以为有组织者,但其实没有,都是我们自发的行为,真的没有组织者。他们就抓人,到处不停地问谁是组织者,你有没有头头,其实没有啊。
东京也有活动,我当时住大阪,当天刚好在东京办点事情。那天有一个朋友在line群里说,当晚有活动,要不要去。我说我一定要去,当晚就去了,当时也遇到了几位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东京的新宿西口地铁站那边(集合),地上摆了很多鲜花,然后我们就给日本人解释、发传单、说中国现在遭遇什么状况。
后面一个环节,其中一个组织者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就出来说。当时有一个女孩子很厉害——她说她一个月之后要回国了,但她还是出来讲话了,也没有包得很严实,只是戴了口罩而已。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当时我和在现场认识的一个女生,一起纠结要不要讲话,我们后面都出去讲话了。
我当时把口罩摘掉了,上去就在那边夸夸乱讲。
我说,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在上海经历过三个月的隔离。我也知道08年之后,他们为了所谓的“反恐”,对新疆的管控一直非常严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还是愿意站出来去抗议、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是很勇敢的事情。我觉得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三年他们没有任何的悔改,为什么不把人当人看,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三年它不仅没有任何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而且我觉得去年上海、甚至全国能这样被封锁,也是因为我们的默许——所有人的默许——你不发火,你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你觉得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才会这么去做。这是因为我们整体的性格吗,还是说东亚人的儒家文化导致,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都默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没有办法,大家都要保证家里的安全——说实话,如果我没有家人的话,我可能不只是在东京,我在中国做这种事都无所谓。现在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我应该会在30岁之前归化——就是拿到日本的护照,目前是这样的打算。
你当时在日本摘口罩上去讲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不害怕吗?
我是那种很冲动的人,做一些事不会考虑太多,就是觉得我要这么做。你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站出来,但如果你自己能先做到这一点,别人看到你的行为后可能也会这么做——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每个人都必须要先勇敢(地站出来),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心态上的转变,有能力做出这样勇敢的行为。
而且我觉得,更勇敢的是国内那群朋友们——他们是冒着被打、被抓、甚至可能会在局子里永远不会被放出来的风险——包括在北京四通桥的人,和他们相比我做的事不算什么,他们才是更勇敢的那种人,他们是豁出了自己的人生吧。
你在日本会和中国同学聊一些比较政治化的东西吗?
我会谨慎。我原先在国内时一直会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一些言论,但是我来到日本之后,发现很多国人并不这么想——来日本之后,发现大家怎么都这么爱国呀,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子——尤其是很多男性,他们就是那种不爱国不行的程度。
我在这边的话,是尽量少跟中国人玩,而且我会挑人。如果刚认识的话,我可能会试探一下——如果我觉得这个人不太行,我就会停止聊天。因为我觉得在海外是要当心一点,毕竟我现在没有拿到护照,还是比较危险的。就算我拿了绿卡,那还是中国的国籍,是不安全的。
之前那个核废水的时候,群里认识的一个小伙伴回国的时候护照被剪掉了。海关好像是说什么,外媒太危险了、日本核废水太危险了、你应该在国内好好待着,当时反正护照被剪掉了。但是还好,没有影响他再出来,他后来还是应该有回日本。但我现在很怕这种事,很怕我回国出什么事,就是在海外还是要当心,要防自己人——尤其是在这边的中国人,可能会有被举报的风险,所以我会比较当心,不太跟这边很多中国小留聊天。
因为我们能出来就说明家庭条件不差,大家其实都是有吃到红利的,都有一定的特权。另外很多体制内的家庭——他们知道这个体制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才会把孩子送出来,但是他们又还要享受体制内的红利——他们反而是会比较亲体制的。
你家里人会怎么看国内的情况呢?包括你自己跟你妈妈出柜,她什么反应呢?
其实我觉得我妈应该很早就知道我喜欢女孩子,但是她不讲,她就装着不知道。对父母出柜这种事,我其实觉得不是很重要——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只是告知他们而已,不管我喜欢谁,感情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只是告知你,你接不接受是你自己的事情。当时我跟我妈出柜,其实也不是直接出的——我跟她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她说,你说呀。我跟她拉扯了十分钟,她说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喜欢女生。
我就知道,她原来早就知道,她装不知道。我跟她说,我怕你不高兴,她说,没办法,你是我女儿。但是我觉得她可能心里还是会觉得我现在在玩吧。不过我觉得近一年,我来日本之后,她可能接受度高了一点,也没有再催我什么的,我甚至直接在她面前大声讲,「我喝了日本核废水变成同性恋了」。
那你还会和家里讨论现在的社会情况,包括你自己一些政治上比较激进的观点吗?
我妈是上海人,但她其实是在新疆长大的,后来才回到上海的。我觉得她们可能不关心,或者不敢去关心——她们就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给你颗糖以后,你觉得前面吃的屎都没关系了。她们不敢去谈这种问题,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放在台面上讲,这种事发生就发生吧——我觉得她们习惯这种压迫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她们在国内,其实不太方便聊这些事情,手机监控太厉害了。我想尽量避免在国内软件上讲一切的政治问题,毕竟会有点不安全。
那你觉得,参加东京的这个白纸活动,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政治活动。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就是觉得大家都很厉害——我们甚至没有组织人,但是我们却如此团结;我们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却像一家人一样——每个人都去为一些…不太可能改变的事情,去为它抗衡,为它努力斗争。我以为那是个开端,是一个起点,会鼓舞很多人——你的人生究竟做过什么,这辈子你到底有没有为你自己的权利去抗争过。如果没有这次白纸事件,没有人民的这种抗争,我们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完全解封,所以我当时觉得所有人都非常勇敢。
我原以为今年应该还有类似的抗议,但没有,过去就过去了。大家永远都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家都记不住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害怕的是这些事情被遗忘吧。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像这样的一个运动,很难得,真的是从未见过的。
我自己在国内经历那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你会觉得你不能闭嘴,你一定要持续地发声。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发朋友圈,每天都提自己的意见。但是我发现来到海外、来到日本之后,我说得反而少了——因为我在日本没有这种压力,我没有受到这种迫害,活得很轻松——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麻木了,还是已经不在乎这件事了?但是就算我移民了,我的血液里还是中国人,我没办法去逃避这件事情——所以感觉很复杂吧,最近我也很少去看政治问题了。
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你是怎么理解自己的身份的问题呢?即使你拿到了日本的护照,你依然需要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吗?
我觉得血缘关系没那么重要——只不过是因为责任、亲情、一种花了时间精力金钱后带来的使命感、愧疚感,所以你才会认为你离不开这种血缘关系。我觉得我跟中国是一体的——我的共情能力太强了,我没办法做到完全抛弃国内的所有东西,我依然会担心我身边的朋友以及我的家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讨厌的归属感——就算你拿了其他的护照,你还是无法改变你的身份,很难不去关心自己国家的事情。毕竟你看大家受苦成这个样子,还是很心痛的。但是像我刚刚说的,我到国外之后,确实关心得少了,就是没这个力气、很难去重新投入到这种事情上。
之前弦子在东京做讲座,现场有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年轻人,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会不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或者没办法去帮助到更多人?我记得她也是说,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之前,我们要选择去关心别人。我觉得共情能力是很重要的,不可能换了身份之后,你就什么都不做了,不管别人了。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觉得人活着的意义就没有了。
如果我不关心政治问题,我可能会过得更开心一点——但是不可能,因为我的性格不是那样。现在我可能会关心一下,只不过没有之前那么高亢、那么激烈了——因为之前在国内这三年真的是太恐怖了,说实话很痛苦。反而到东京这边之后,我会更关注自身,因为我觉得社会问题是人造成的,如果说我要研究社会问题,那我就要从自身出发——人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有这些社会问题。
所以在国内的时候,你的对抗感会更加强烈是吗?
对,我那个时候是什么都要讲两句,就是很不满。反而来到海外之后,我变得更平和一点,会更关注自身的生活、自己的学业——反正新闻看得少了,微博也看得少了。
现在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再像之前那个样子——每天一直哭、一直去关心那些问题的话——我可能会非常内耗,因为我改变不了任何政治问题。白纸运动那么激烈,发展到全国,但其实都没开始就结束了。
你最早是为什么会想说去日本?
19年那时候我身体不好,刚确诊基础疾病,我妈的朋友就问我要不要去日本生活——反正费用也不是很高,家里负担得起,再加上医疗条件确实是真的好。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学艺术的,我爸爸是摄影师,我自己也对摄影很感兴趣,就来日本学摄影。我对我自己的未来规划非常清晰——之后要做什么、怎么做、跟谁合作,我都已经想好了。移民的话,日本的护照含金量非常高,全球100多个国家免签,对于像我这种做艺术的人来说很适合——我可以全球到处跑,去工作或者出去玩,我本来也是个爱玩的人。当然我也考虑过去欧美,但是日本肯定是我长期居住的国家。
那日本这边的新冠疫情算是结束了吗?有关注到民众以及政府层面中日的区别吗?
日本还是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日本人他们其实有戴口罩的习惯。日本人很在意这种事情,他们会戴口罩,电视上也(看到民众)戴口罩。我无所谓,但是去一些场合有要求的话还是要戴的,所以随身会备个口罩。日本是今年3月份正式说,我们不用戴口罩了,正式解封,之后几乎就没有人戴了。
我目前在日本没有遇到过歧视什么的,整体还蛮友好的。但是疫情很严重的那段时间,也有人发视频说,日本人在店门口贴“中国人不要进去”的标识,说“武汉病毒不要进去”。当然我觉得更多是老人家不理解,老人他们可能会害怕,但是年轻人还好——日本年轻人都是比较随意的状态,还是蛮友善的。
中国人比较爱热闹,但是日本人不会,日本人很有边界感,我觉得这一点东京跟上海非常像——就是他们不会去打扰你的生活,我们都做好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就好了,不会去让别人感到困扰。而且在吃喝玩乐方面,东京的物价比上海低很多——除了交通费,物价真的是很低,包括租房买房都比上海低,上海的物价我就觉得挺吓人的。
你说从小都很坚定要做艺术和摄影,你会觉得这几年的经历,对于你个人的艺术创作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我原先做摄影,只是喜欢拍照——我没有太明确的目标,没有特别想要去做什么主题,就是拍着玩。今年刚搬来东京之后,我对于作品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为什么比起血缘关系,我们更倾向于非血缘关系。你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更能相爱、更能有那种(深厚的)友谊,是一种chosen family。我很在意这个点——我的国籍、性别、家人都是不能选择的,所以我会觉得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去选的东西是更重要的。
其实比起比较大众化的社会问题,我会更关心自我,从自身出发去探究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经历疫情之后,这是我对于自身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艺术就是一种探讨,它更加贴近生活本身,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你的作品,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生活经历当然对我的作品有重要的影响。比如说我不能出来的那两年,我在上海参加了骄傲节、LGBTQ+的活动,20、21年的我都参加了,线下和大家交流什么的。那两年也有在打工、跟外国人交流,这是我的社会经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做这些作品的一个(主要的)出发点就是家庭——我感觉我永远逃不出家庭这种钢筋混泥土的结构,比起让他们认同我、让他们接受我,我为什么不自己去改变呢?我不如算了,不跟他们内耗了,我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也是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才会有新的想法。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的感情生活。我谈过的历任,她们给我带来的一些东西、给予我的支持或者不支持,都给了我很好的成长,我觉得这很重要。我的作品的主题叫“不由自主的爱”,它跟爱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家庭和生活,这个作品的一部分也来源于我跟我的前任们。
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上海的LGBTQ社群里面的经历?因为上海骄傲节后面也关掉了。
其实我19年就参加了。19年没有太多线下活动,好像当时是被举报了,那年我可能只是去创意园看了展。20年的话,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第一任女朋友。上海骄傲节从3、4月份开始,一直到暑假都有活动,比如有一些酷儿心理讲座,近几年会关注一些跨性别群体的讲座。还有线下的酷儿跑,跑步的活动,跑完之后大家一起吃brunch。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电影周,那些领事馆——什么德国、芬兰、瑞典领事馆——他们会播放LGBTQ+的电影,你去领事馆那边可以免费看,还会有主讲人来分享这个电影。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他们每年都会有那种粉红派对pink party,在上海的珍珠剧场。那个地方真的很好玩,我觉得是全上海最好玩的吧——它跟那种传统的夜店不一样,有点像个小的歌剧厅,大家可以喝酒聊天;但它的氛围不像那种很吵的夜店,大家真的是在很开心地跳舞互动。
说实话,一般来说是中上层的人才会参加这些活动。包括举办这个活动的人,他们其实是有利益可赚的,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在性少数群众中吃得到某些红利的。主办人好像是一对拉拉(couple),现在在澳大利亚。但是到21、22年他们被举报叫停了,上海就再也没有骄傲节了,我觉得蛮可惜的。虽然有所谓的利益关系,他们可能要赚一些钱,但是你(性少数)在国内本来发声就比较少,没有什么参加活动的机会,然后连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活动都没有了。被禁止的东西越来越多,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上海现在没什么好玩的。
那么你是怎么理解你自己做的东西的意义?艺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我是真情实感地想要去关注性少数群体。那其次,它当然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它是一种语言——如果一个人能看懂你的作品,那这个人一定很能理解你、很能和你共情。当然艺术肯定也是一种自我,自我也是一种艺术——我觉得人做的东西主观性都是非常强的,它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自己的情感、思想之上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其次就是艺术也是一种政治、是一种批判行为。我近几次考试都提到,(艺术)它是一种我们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别人的想法的方式。之前香港的那个运动,我记得当时有朋友去拍了照,就是即时摄影,我觉得这是一种表达方式——我为这个东西抗议,我去表达我的不满,其实就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可能当你不能明确地用声音讲出你的想法、你不能批判这个社会、你不能批判你的政府、你的国家时,只能用艺术这一方式——因为它可能不会危害到你的人身安全,这也是对你自身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艺术是很包容的,它包罗万象,是我的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于你来说疫情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它结束了吗?
我(22年6月)落地香港的时候,自我宣布疫情结束了——我觉得它(疫情)的另外一面就是一种压抑,我宣布这份压抑的情感,它对我来说,结束了。
但是说实话,也没有真正结束,因为我们还在为此抗争、还在为此发声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情感还是蛮复杂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疫情明面上算是结束,但是私底下,其实我觉得每个清醒一点的人,都会很明白这种事情它无法结束。我们真正该去抗争的,不是说疫情是否结束,而是我们能否真正自由。
6月4号上海解封的那一天,我并不开心。我身边很多人都出去通宵玩了一晚上,但我会觉得,大家真的能不记得这种事情吗?你们怎么会像当没发生一样地出去玩呢?我不是说强制性让大家不要出去玩,但是我觉得你们要记得,你们不能忘记这种事情。我觉得这种耻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默许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你允许别人伤害你,他们就会伤害你。
那你觉得现在大家还记得吗?
有些人会记得,会放在心里,但有些人会选择性忘记,因为他们不想提起这件事情。
你觉得是因为痛苦还是因为害怕?
我觉得是害怕吧,很多人是害怕。不敢讲,毕竟这个大环境下,只要你没有移民,他们是有权伤害你的——我觉得中国是没有法律的,也害怕身边的人受到伤害。当然痛苦肯定是有的,但是害怕可能更多一点吧。
我们其实已经不太(和朋友)提这些事情了。跟我经历相似的本身也不多——很多朋友他们不是在上海经历的疫情,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回国,可能无法体会到这种痛苦,或者很难真正去共情,很难亲身地体验到这种感觉…所以我不提——不会刻意去提。很多中国人会(和别人)提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多痛苦)。原来我是这样的,现在我也不讲了。因为一遍又一遍,讲来讲去,会觉得自己有点麻木了吧。
对于你来说,这三年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份记忆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间。
哪怕比起疫情,我都觉得这段关系是我自己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跟前任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我为数不多的很开心的一段时间——可能也有吵架,但是是真心实感地觉得很幸福的。想跟这个人在一起很久很久,不会想要分开。
我这次做的作品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和很喜欢的人在一起再到分别,也是我决定做这个作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爱是一个很庞大的题材,我原先在想要不要去触碰这个题材,因为感觉很难讲清楚自己的观点,爱很抽象。后面我做这个作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她的爱——这个作品就是讨论我们为什么会被血缘关系束缚,但反而在非血缘关系当中可以跟对方有这么深刻的连结。我跟我前任也是这样——我们不是由血缘关系建立的传统家庭,但是我们依然想跟对方有深刻的情感连结,这个人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对方,我们想要变成彼此的chosen family,彼此的家人。
她就是我的家人。
不知道有没有跑题。(笑)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很个人也很美好的——这个我问过很多人,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提到一些非常痛苦的状态,但是你说,定义你三年的瞬间是和爱人在一起的很动人很快乐,我觉得真的很美好。
关于这三年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补充的东西吗?
其实我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不太喜欢行动的样子——比如说要做女性主义,但其实我们线下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它像一个魂魄,我们有点虚无缥缈地在活着,但是大家没有具体地去策划什么行动。我觉得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立马去抗议,不是这个样子,但比如说做线下活动的话,可以开始办一些讲座,我们去共同进行一些讨论,而不是在网上假大空,所以我就会觉得年轻人丧失热情了吧。
那关于未来,你现在有什么计划或者想象吗?
大学我应该会创业吧,跟别人合伙做个小型工作室,赚点钱。
纯艺类型的东西不可能养活我自己的,所以除了做一个关于自己的作品——就是比较纯粹的一个作品——我可能也会做商业类型的一些摄影,之后也想要做一些策展的工作。等拿到日本的护照之后,除了在日本活动以外,可能也会经常去去欧美跟别的艺术家进行一些合作。当然我想要这样飞去欧美,也是因为想要跟前任保持关系,所以说这也是目的之一吧——我对我自己未来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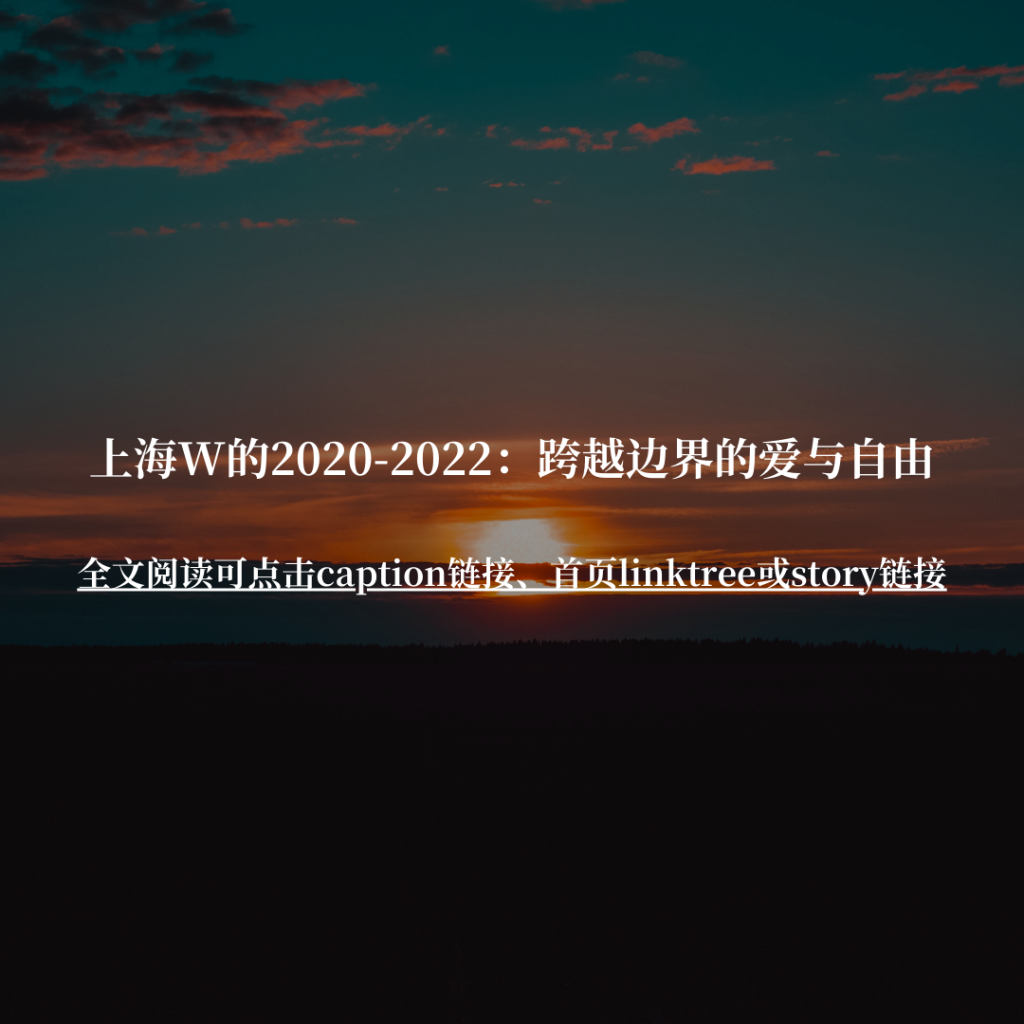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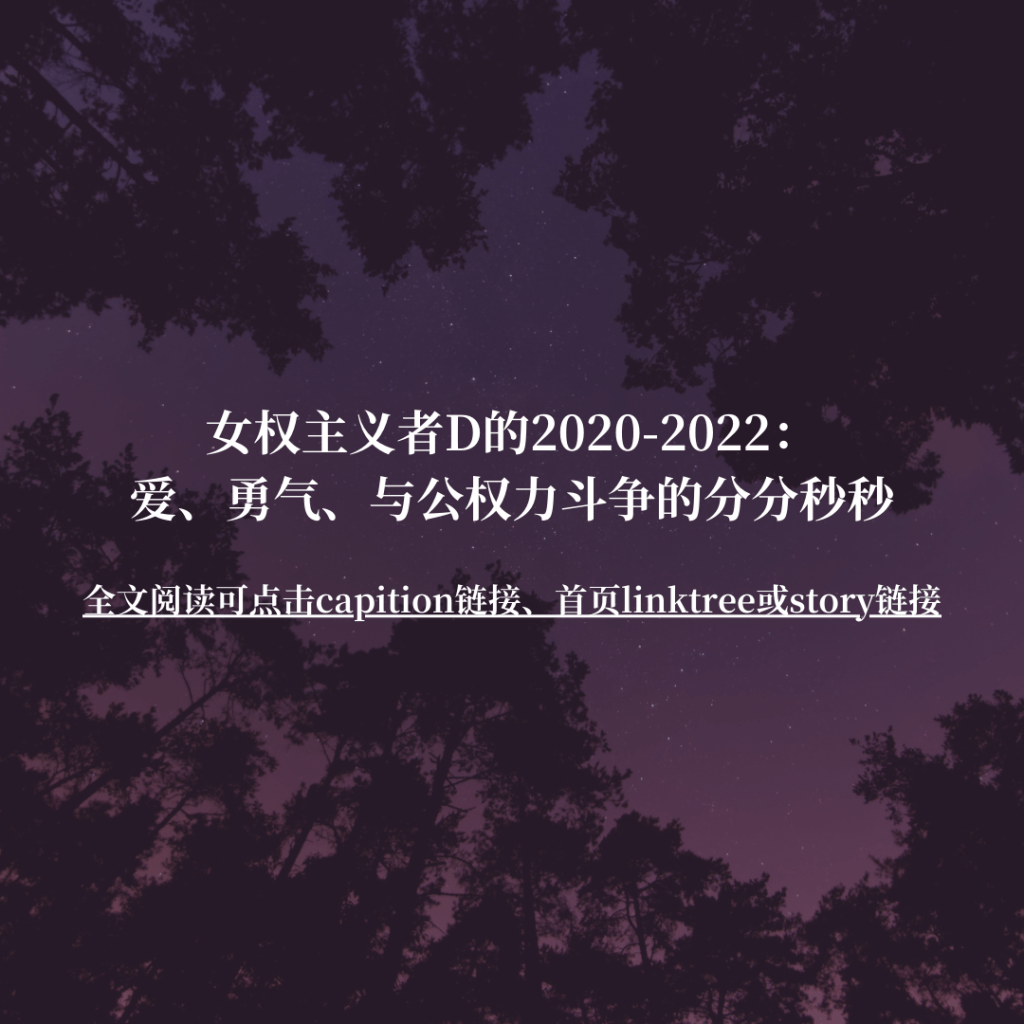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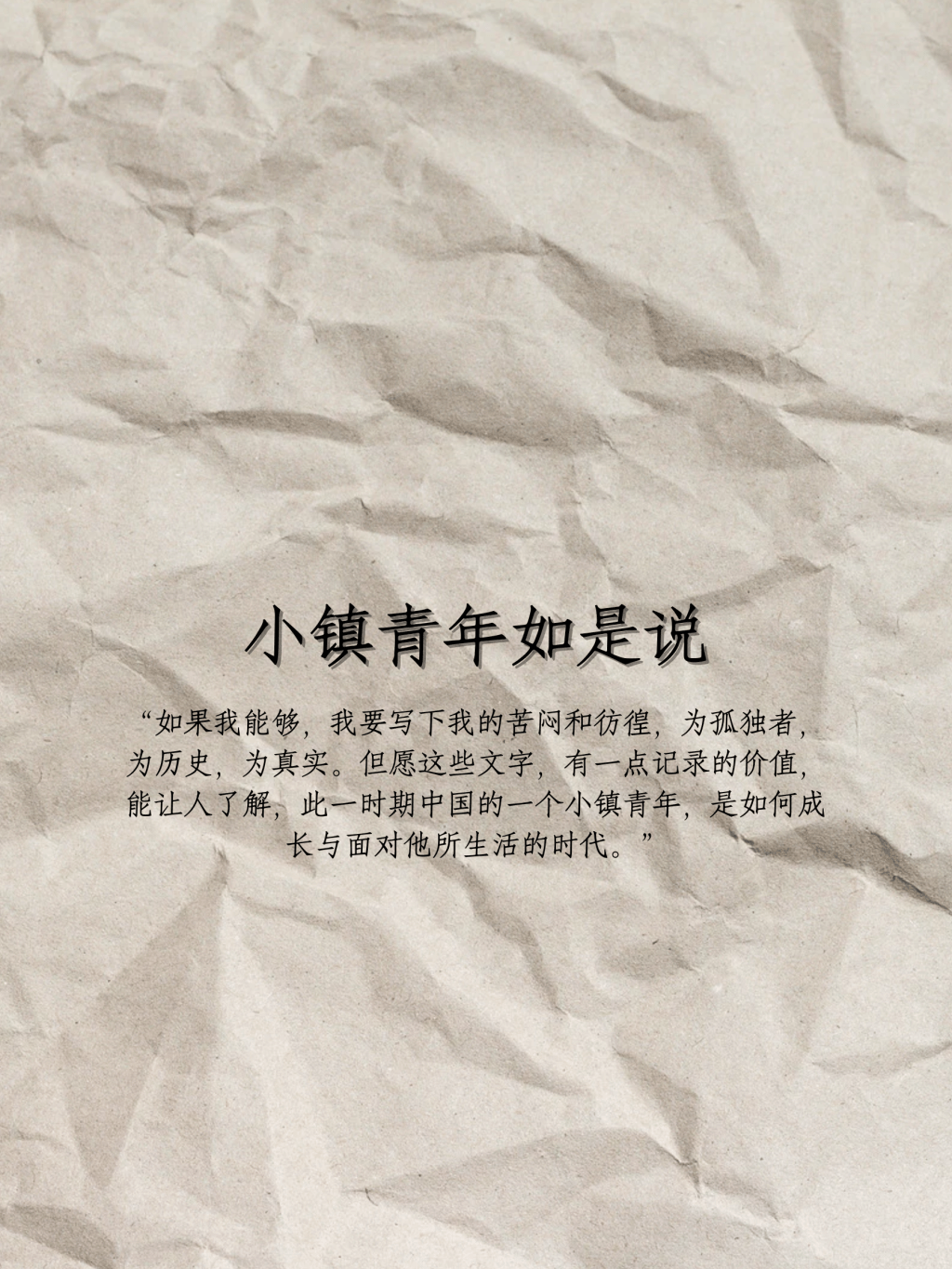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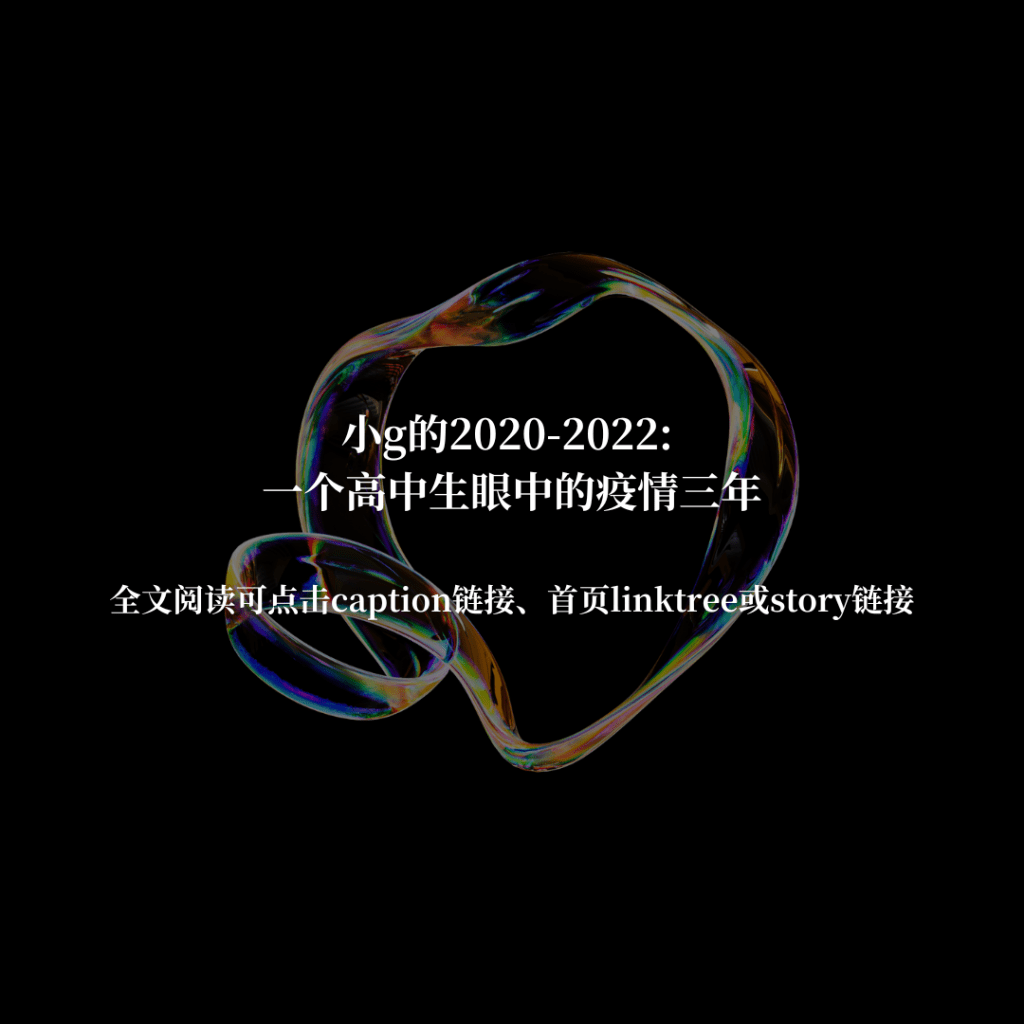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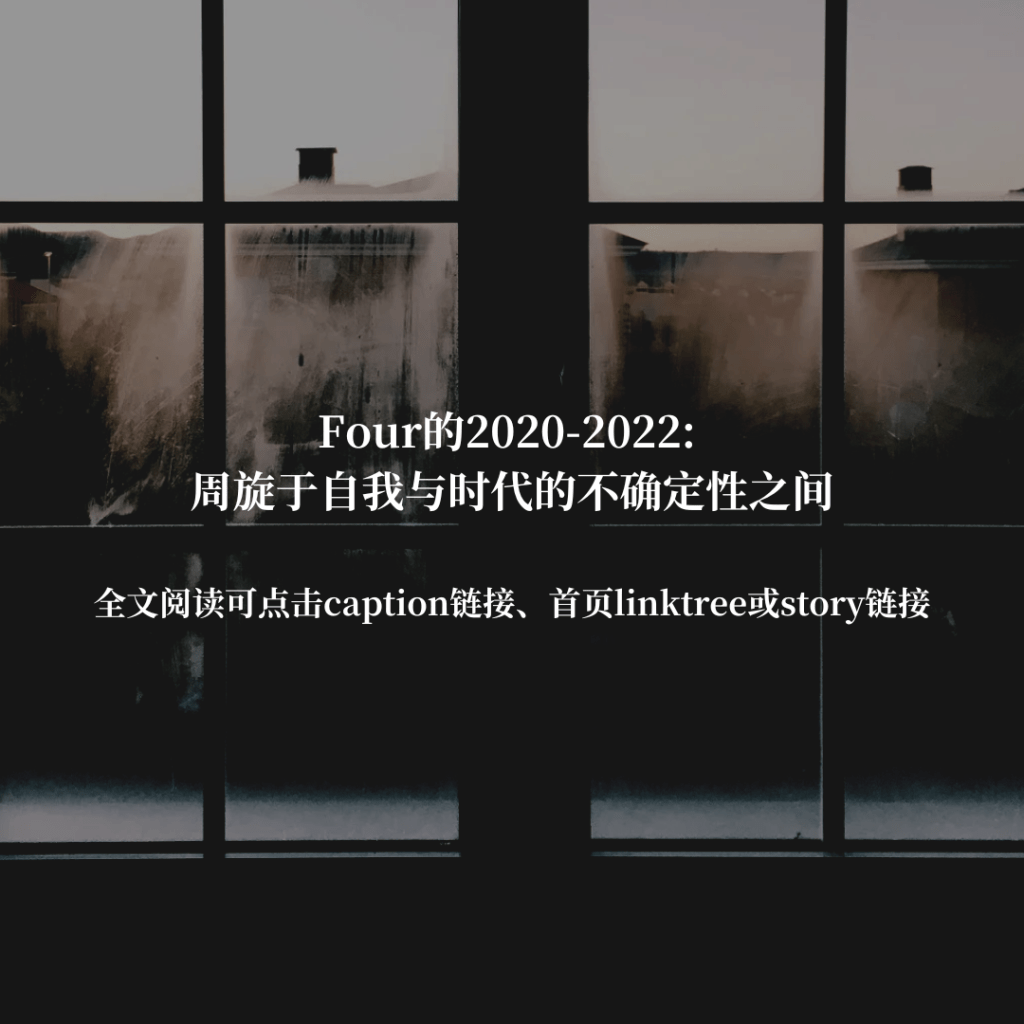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