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应物
职业:背包客
年龄:00后
性别:男
标签:vipassana练习者
2020-2022所在地:成都 南方小镇
现在所在地:在路上
(本文包括标题在内的所有内容全部来自投稿者,本项目志愿者仅做有限校对)
小镇青年如是说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苦闷和彷徨,为孤独者,为历史,为真实。但愿这些文字,有一点记录的价值,能让人了解,此一时期中国的一个小镇青年,是如何成长与面对他所生活的时代。
PART I 楚门的世界
三年疫情,深刻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回首往事,变革的潜流在更早就已悄然汇聚,只是随着疫情危机的不断强化而日渐汹涌,最终喷发而出。
我出生在一个小镇,确切地说,是一个「曾阔气过的」南方城镇。三线建设后,当地工厂林立,父母都是单位职工。我是00后,刚出生后不久,父母就经历下岗潮。童年里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在书上读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形式上,工人的地位被摆得很高,但放眼自己周遭的生活,下岗潮后,留下的是大量离婚、留守儿童与贫穷。残酷现实与虚假宣传之间的冲突,成为我思考的起点。
(我的)成长阶段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矛盾丛生,亲历了许多不平等,贪污腐化的问题。它们也是思想成长最好的催化剂,让我与官方宣传教育灌输的内容日益疏远。那是一段漫长而煎熬的岁月,在此时期,我常常既怀疑世界,又怀疑自己。当看到社会上那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时,或愤怒,或失望,但环顾四周,人们却是一幅习以为常的姿态,要么就装作歌舞升平。我感到不知所措。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我察觉到自己生活在某种谎言之中,但疑问得不到解答,真实也无处可寻,更无法诉说内心的苦闷,只能拧巴地活着,独自默默思考。同龄人要么是专心内卷,拼命成为做题家,要么就早早辍学打工;我则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一面也不得不努力当个做题家——因为考试升学,是我离开当时环境的唯一办法——另一方面又极其排斥应试教育,想尽办法去找各种课外读物,开拓另一个精神世界,逃避被规训的压抑。与大城市不同,小镇没有那么多资源去了解各种批评与异议思想,只能读到新华书店里的那类东西。
高中考到了市里,虽然也只是一个四线小城,但能读到的书,终是比小镇丰富得多。《看天下》《三联生活周刊》等杂志是最早的启蒙读物,让我逐渐有了更多的渠道去了解社会变革,眼界也日渐开阔。但受限于中国的审查制度,其文章尺度有限,始终感觉有层窗户纸没被捅破,缺乏足够的批评性。多年后学会翻墙,读到了《长平观察》,才知道什么是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新闻报道。
读到《1984》时,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几十年前外国小说中的情节,在某种意义上,和我当下的生活竟如出一辙。我察觉到一种共通的历史处境,找到了长久以来渴望的强烈共鸣。怀疑得到验证,那些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专制带来的压迫与系统性暴力,那些颠倒是非,那些欺骗——所有的问题并非我个人的臆想,而是真实存在的,且制度性缺陷由来已久。我感到不再孤单,找到了某种归属感。
那时也曾想过去学会「翻墙」看看墙外的世界,在没有了言论钳制与思想审查后,人们真实的看法是什么样。但又担心,倘若果真掀开伪装,某些真实恐怕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原本的生活或许也将天翻地覆。这种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对高中的我来说过于奢侈与沉重,我仍然要以成为小镇做题家为目标,这样我才能去更大的城市,有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一个更现实的方向。但当高考结束,进入大学,学会翻墙后,结果也确实如前所料,一切都开始天翻地覆起来。
PART II 红色药丸
来到成都,开启了大学生涯,应试的压力随之骤减,我半吊子小镇做题家的生活也自此结束。学会翻墙后,立即搜索天安门事件,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大饥荒,香港反送中等一系列冲突。过去在墙内,由于严格的审查,那些敏感内容,要么只能找到一鳞半爪的信息,要么只剩下一面之词,如今终于能更完整地了解来龙去脉了。我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相关信息,由此逐渐重构了历史认识,摆脱矩阵,回归真实。
在经过常年的瞒和骗后,重塑认知,是一个极其挣扎的历程。随着了解的深入,过去的拧巴逐渐解脱,但随之而来的是虚无和痛苦。被打碎的不只是那些虚假宣传,还有与之同构的整个价值体系与经验,而独自觉醒,更平添了一份孤独。我能理解那些人——即使他们知道了中共暴力与血腥的历史,也依旧拒不接受——否定过去绝非易事。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我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巨大魔力所震惊,其竟能如此长久、广泛地进行欺骗,在那些美丽的口号背后,究竟掩盖了多少暴力与谎言?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亦或只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抹黑捏造?
鲁迅曾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旧日鲜血并未被忘却,文章还收录到大陆的教科书中供后人学习。可中共发动的天安门屠杀却被遗忘了,忘得一干二净,年轻一代一无所知。我对中国专制下宿命式的流血牺牲感到悲哀——中共曾是热烈的反对者,为何如今也走到自己曾经的对立面了?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我陷入巨大的茫然之中。疫情的出现恰逢其时,为我提供了喘息之机。让虚伪的更虚伪,让疯狂的更疯狂,乃是令真实呈现的不二法门。疫情期间生活的停摆,让我有大量时间去专注处理个人的精神危机,同时进一步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
刚进大学就被关了三年,便自嘲为「新三届」——老三届上山下乡,新三届封校锁家,两代人的经历大相径庭,时间相隔久远,相同之处,可说是痼疾仍存,还是处在极权制度的束缚下,一样的身不由己。我们是同一代人,包括六四等事件不只是历史,而是政治现状。疫情三年是重大转折,重新塑造了很多人的思想与政治立场,但愿多年后回顾历史,多难兴邦,这代人能广出英杰,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自由。
起初也曾心存侥幸,算是个改良派,认为天安门事件等都是些陈年旧账,要向前看。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悲剧不会重演,鲜血不再流淌,总会好的,政治改革会逐步进行。但疫情时期,各类疯狂的政策与事件层出不穷,加之对历史再认识的不断深入,逐步推翻了旧有的立场,彻底看清了那套在脖子上的枷锁。文革之后,中共为应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稳固统治,才进行了改革开放,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其对权力的垄断从未放松,借助疫情危机,权力又加速从幕后回到台前。
疫情初期,虽初面对严格的封控不太适应,但政策相较于后期封控的僵化与严苛,仍有不错的效果,且还有相当大的弹性与自由。县城里的日常生活受干扰不大,对我来说,更多的麻烦来自思想上的困惑。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那时我每天都去体育馆游泳,回家后继续探究那些疑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越发深入。耳熟能详的诗人北岛竟是流亡者,「海外民运」「人权律师」等各类新词也逐渐走入了我的视野。这才知道在另一个中国,一直都有着大量的反抗者,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奋力斗争……2020年6月4日,郝海东的“新中国联邦建国宣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郝海东常因语出惊人,被人唤作郝大炮,作为一个球迷,我对他非常熟悉。相较于那些过去的历史事件,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我同处于当下的时代,其言其行对我更有切身之感与冲击力。视频一经发出,一夜之间,他就从国内互联网上消失,似乎此人从未存在——《1984》里的描述照进了现实。过去虽也见过此类封杀,如毕福剑,但那是私底下的谈话被泄露;郝海东则是自觉主动的抗争,他很清楚自己的抉择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为他的勇气和道义而震惊,受之感染,也决定彻底转变立场,自觉站在另一种历史叙事与公共记忆一边。后来,任志强、严歌苓……越来越多的人,在疫情时代做出了新的抉择。
2021年清明节,我前往重庆沙坪坝文革墓,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全国很多文革墓以这种或那种原因被拆除,尽管此地保存较完整,但官方也要求「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网上查到清明节可能会开放,我决定去碰碰运气。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过去的问题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自动解决,问题依旧悬而未决,首先,我们需要记住他们。
公园周边车水马龙,里面游人如织,但若非知情者,绝不会想到,在这繁华喧闹之处,竟还隐秘地藏着一座墓园。皆因墓园四周树林密布,将一切悄然藏匿。下午,我走近墓园,大门依旧紧闭。正当我准备顺着门缝往里看时,台阶下的岗亭突然冲出一名保安,凶神恶煞地质问我姓甚名谁,怒斥我「立刻离开」。
我扭头就走,但并未远离,仍旧在公园里四处打转。直到黄昏来临,看到岗亭无人后,才从树林边绕到墓园后侧,决定翻墙而入。高耸的灰墙布满铁丝网,只有在拐角处留下些许空隙,我爬上大树,然后从夹缝里艰难地溜了进去。
墓园里一片寂静,气氛庄严肃穆,和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图片一致。不同之处,不少墓碑前都多了些鲜花,看来今日前来的扫墓者不少。就在我环顾四周,观察墓园时,一抬头,猛然发现了一个摄像头,正射出红色的光线,直直地盯着我。


图1、2 : 文革墓园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1984》里的名言立刻浮现在脑海,我浑身冷汗直冒,手足无措,如同待宰的羔羊一样,呆呆地伫立在原地。温斯顿被抓的场景不断闪现───身穿黑色制服的壮汉破门而入,凶狠地把我打倒,而后带走审查。我不知被定住了多久,而后突然惊醒。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我仍心惊肉跳,立刻翻墙离去,似乎再待下去,就会被墓园吞噬,随夜色一同埋葬于此。
再随便谈点关于头发的趣事吧,与诸位同乐。恰好二十大期间我留了脏辫,朋友问起原由,便半开玩笑地说「皇帝要坐龙庭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趁早留辫子迎接复辟罢。」习近平果不其然开启了第三个任期。
学校有一领导,见我留长发,便责备道「男生留长发,像什么话,男不男,女不女的。」这话令我诧异,但也在意料之中。我知道在今日之中国,仍有正人君子之流是见不得男生留长发的,只是没想到大学老师的思想竟也如此封闭——这正是我留脏辫的一个小缘由,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便回呛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但有些人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演着旧戏码,一样的头发问题,一样的狭隘,一样的专制。巴金的《家》,在近一个世纪后的成都又复活了,同倩如一样。只不过从前的批评者是书里的流氓,现在摇身一变,改名叫领导罢了。
辫子,是很不容易剪掉的。
PARTIII 呐喊与彷徨
成都白纸运动发生当天,我先是在朋友圈看到了那张海报,号召大家前往望平街悼念。大概是受其他地区抗议活动的影响,之前还能正常进出的校园,那几天便借疫情管控之名,又严格封闭起来。学校还专门发布通知,要求密切关注同学们之间的思想动态,避免舆情。但有同学家在成都,恰于封闭前回家未在校,就把海报发给他,他于当晚前往参加了悼念。
当晚,我一直在校园里四处打转,试图找到监管松懈的地方,偷偷溜出去。但那时的监管却异常严格,四处都有保安不断巡逻。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和同学保持着联系,但信号时断时续。他陆续发来现场的情况,我都保存下来,想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保留下一些材料。
除了这位同学,还有个微信群,其中多为异见分子,也有人前往参加了悼念,都在不断转发着现场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悼念的人群不断聚集,火药味逐渐浓烈,抗议的口号也随之升级。但那时我身处的校园,却仍旧如同往昔,微风轻拂,一派安宁和谐之景,什么都不曾发生,似乎处于截然不同的世界。
校园中的大多数人对这场抗议一无所知。如果我也袖手旁观,那就意味着我同他们一样,默许防疫政策的不合理与造成的灾难,对一切不合理的管控都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我必须要采取行动,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来表达我的抗议与对死者的哀悼;我必须离开此地,汇入抗议者们的洪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逐渐按耐不住这种反差的压抑,在苦寻偷溜(方法)无果后,我便打算来硬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骑车,快速冲过校门口的安保。但当我真骑着共享单车,距离出口只有几十米时,却立在了那里,只是呆呆地望着校外,怎么也迈不动腿了。关于四通桥事件的记忆逐渐袭来,恐惧与担忧蔓延全身。
四通桥事件发生当日,正好家人打来电话,就顺便与他们谈起这事。未曾想到,后来爷爷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告诫我注意安全,坚决远离这类活动——他了解天安门事件,很清楚共产党镇压的残酷性。「软肋」视频那两天方兴未艾,中共这下确实抓住我的软肋了。如果是身处抗议纪念的人群之中,还能够借助庞大的群体来保护自身,可要是就这么直接了当地冲出去,必然彻底暴露。我知道因为抗议已经抓捕了一些人,并且还将继续抓捕下去,要是冲出去,恐怕是有去无回,等待我的只会是监狱。家人怎么办,我会被关多久……激情逐渐消退,理智占据了上风。
那一刻才知道,自己并非孤勇者,也不是坦克人。尽管我并不怯懦,但也不像过去自认为的那样勇敢。那一刻,突然就理解了那些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为什么面对这个政权的暴力与压迫,很多人没有义愤填膺,没有起身反抗,即使是小小的抗议也是稀缺之物?在这样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任何温和的抗议在中共看来都不可容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大众被系统地打碎成原子化的个体,难以齐心协力发动社会运动,抗议往往成为个人的单打独斗。只身一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其中的压力与挣扎,只有亲身面对才能体会。
同学后来告诉我,在他回家的路上,担心地铁附近有人抓捕,便先骑着共享单车逃离了大部队几公里,然后才搭车回家。也许是确有其事,也许是惊魂未定,他觉得一路上都有人跟踪,特别是抵达小区后,大门口立着几个人,一直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似乎在进行无声的警告。
我终究没有冲出去,只好回到宿舍。但不一会儿,学校的保安开始了行动,逐个排查寝室,检查有无白纸——后来听说,当夜校园里也曾有人举白纸抗议。我激动地向室友们谈论着刚发生的一切,他们初感惊奇,而后不置可否,像是在听着远方的奇闻异事,只是一面点头,一面继续打游戏罢了。我渐渐感到自己成了「被示众者」,费尽心力,不过是给看客们增加点谈资。慷慨激昂渐渐消失,最后只剩一阵空洞的沉默。忍不住问起他们的看法,众人突然爆发出一阵喧闹,七嘴八舌说个不停,意思却一样,都认为清零虽然问题多多,但抱怨两句就行,游行到底是要不得的危险举动。熄灯就寝,而后连「莫谈国事」的调子也停了,只余下茫茫夜色。
PARTIV 半个哥哥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gap year,徒步重走长征路。一来,是这几年疫情被关得实在烦闷,又见证了许多生离死别,颇有人生无常之感。便想乘着年轻,游览名山大川,行脚参学。其二,也算是做一次漫长的田野调查——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毛泽东当年写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现在是验收的时候了。很多人在疫情后感到失望,选择了润,但这些多是城市精英的立场。中共各类严苛的政策能够实施,一定是有着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支撑。当代中国广大乡村总是被忘却,被代表,难以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我希望自己能听见另一个无声的中国。
在八十年代,《经济日报》的记者重走长征路,发掘了「半床棉被」的故事,后来当地由此建造起纪念馆,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镇。沿途我也碰见个故事,记录下来,以飨读者诸君。
路过遵义龙坪镇附近村庄,天气炎热,便在路旁一老者家休憩喝水。我知道大饥荒时期,遵义饿死了很多人,就与老大爷谈起了大饥荒,问起当地的具体情况。他说「那个时候大队开会,去的路上,走着走着人实在没了力气,啪,倒在路边,起不来就死掉了。啊,到了会场,连着开几个小时的批斗会,开着开着又有人饿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问他为什么不起来反抗,他说心软的干部受到政治压力与批判,扛不住,上吊自杀了;剩下的大多凶狠恶毒,打骂是家常便饭,再有警察军队给其撑腰,打不过,也不敢,只得老老实实挨饿等死。
我看过不少关于大饥荒的记载,这些不算太新鲜,但有一「人相食」事件让我刻骨铭心。大娘说起她们邻村耕地贫瘠稀少,贫穷落后,丰年粮食不过糊口,更别说大饥荒了。闹了饥荒,家里孩子多,哥哥先给饿死了,无力埋葬,陈于家中。饥荒持续,难以忍耐,弟弟遂砍下哥哥尸体的大腿,烹而食之。
饥荒迟迟未能结束,弟弟又忍耐不住,准备再吃哥哥以充饥。母亲实在是于心不忍,便劝道,「娃儿,那是你亲哥,给他剩点吧。」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但我没看到任何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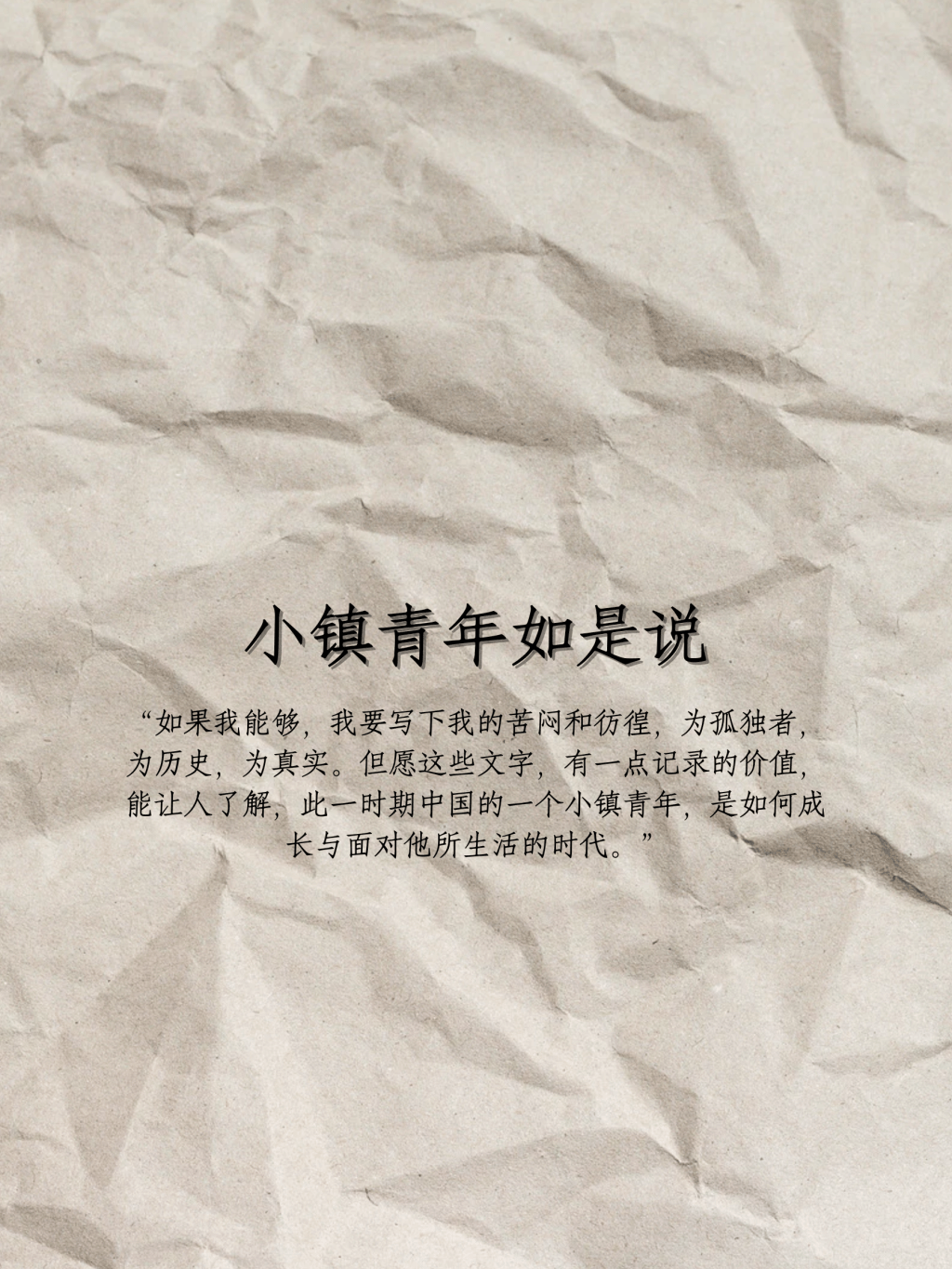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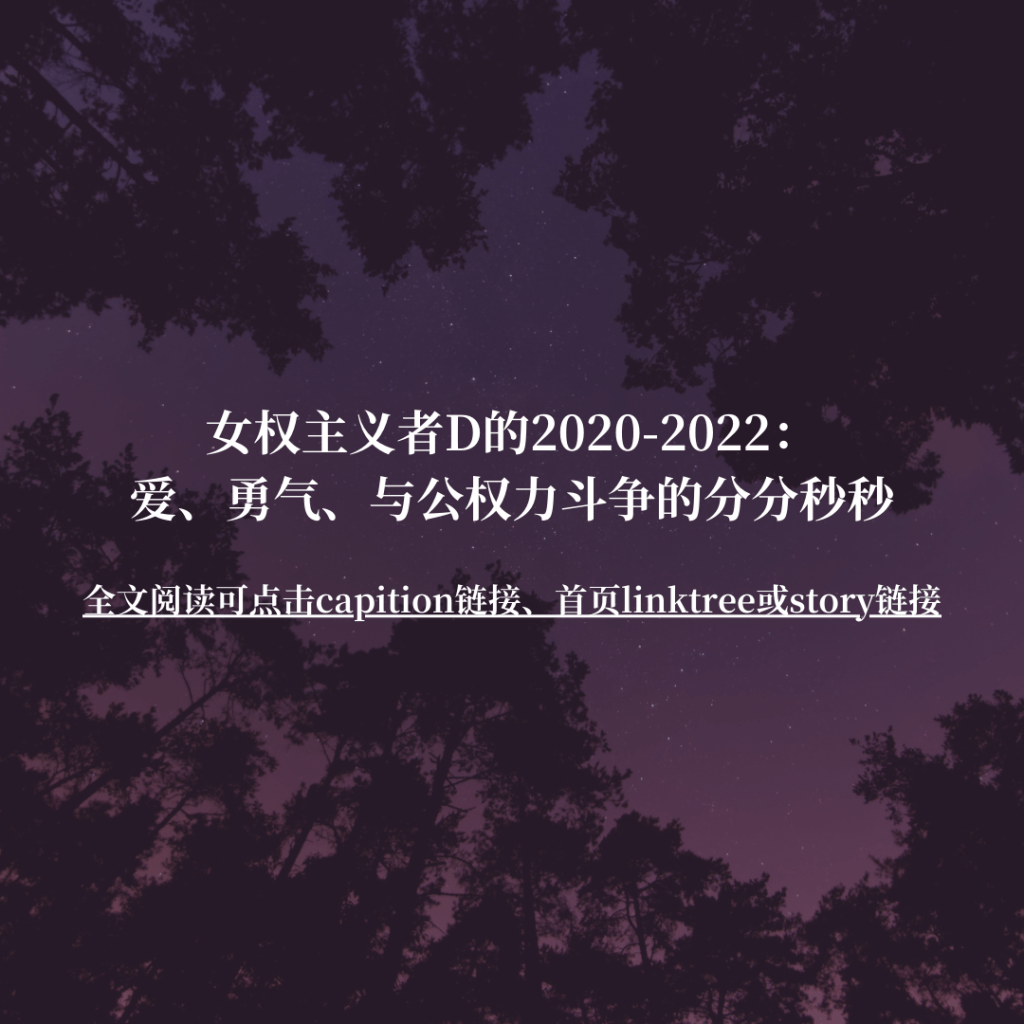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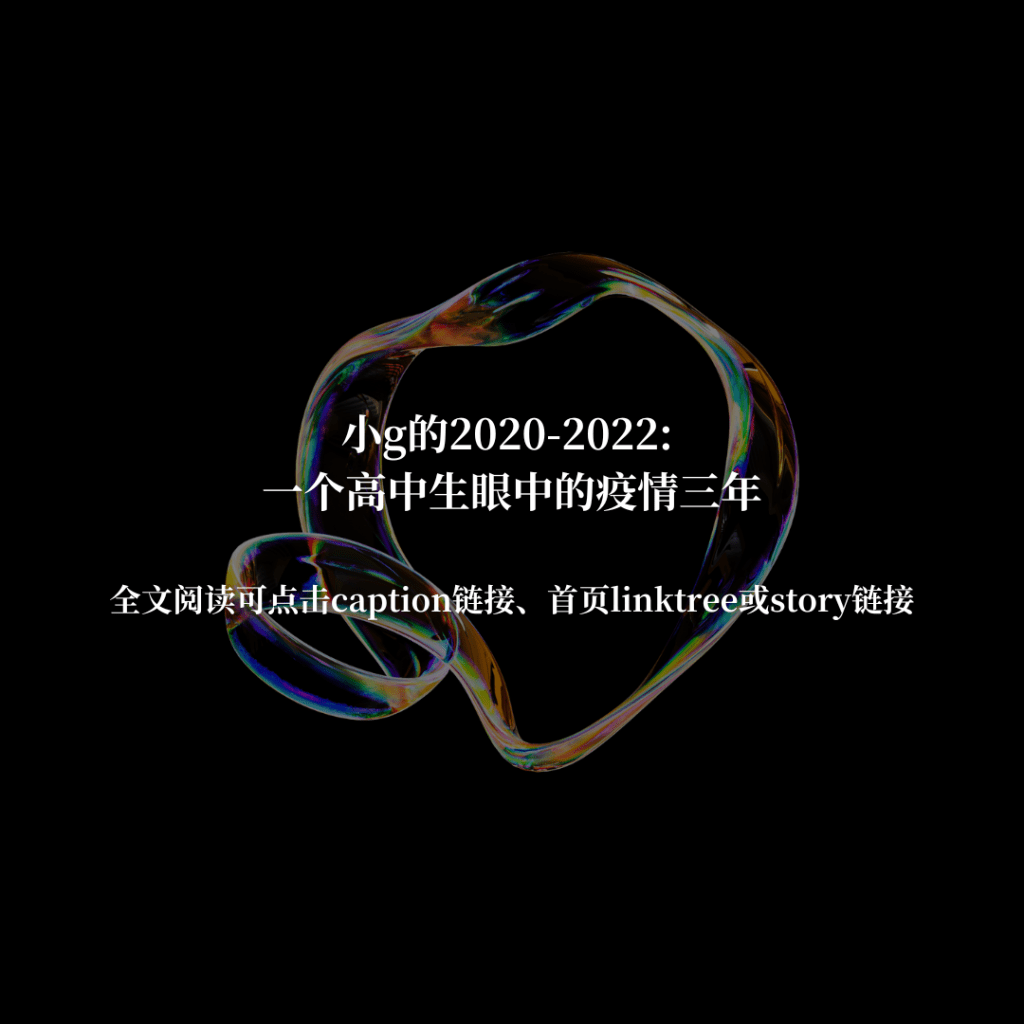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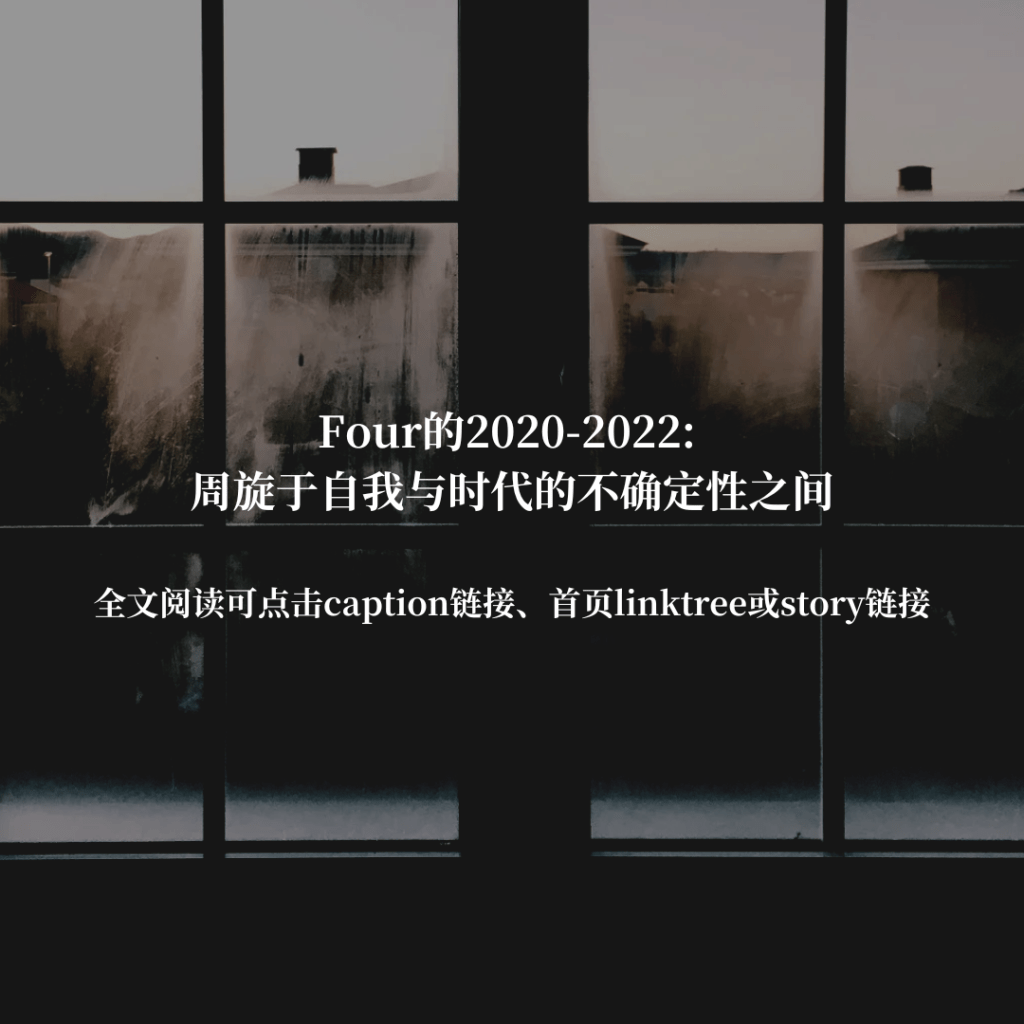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