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Emily
职业:学生
年龄:90后
性别:女性
标签:共情者
2020-2022所在地:北京、天津、上海
目前所在地:纽约
访谈时长:200分钟
访谈时间:2023年12月22日
访谈人:小A
校对人:Chris,Bo
关键词:流动,家庭,留学,见证/记录,离散,社群
PART I
行行重行行
我现在在读第二个本科,主要是在读和经济与社科相关的专业,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非常overlapping的——我本身是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如果对经济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很难光从一个方面来judge… 但是我发现经济学的东西真的好难,比我花在社科上的时间要多太多了,可能这个department整体就是很卷、人很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反正我现在focus还是在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和中国政治这些。
我上一个本科是商科的,学酒店管理加西餐管理,和现在完全irrelevant的行业。(这个行业)疫情当中面临的困难比较大,也让我对各个国家经济、商业模式等都有一些新的看法,因为很多东西(行业)在疫情开始就彻底摆烂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让我看到很多不公平和不确定性。
我曾经觉得餐厅、酒店、服务业都是经济的很大组成部分,没想到疫情发生之后什么都不是了——我所有的朋友、同事全都失业了。那个时候我在上研究生,真的就是毕业即失业——因为我是20年毕业的。疫情期间一切都停摆了,我们上课都没有东西可以做。以往教授会带我们去各种酒店也好餐厅也好,做site visit,但(2020年)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能用的项目例子也都是疫情以前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针对性,就真的是很迷茫。
我本科是18年毕业的。我之前就是做西餐——餐饮管理这种——在纽约的那些fine dining、米其林啊,主打一个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嘛,也是觉得自己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那种感觉,我对这个社会、包括对自己所处状态的一些觉醒时刻,都是疫情这几年有的,所以真的还是挺关键的。我决定再重新回来上学、选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专业,也是那个时候决定的——我是21年申请的,22年回来的。
我20年回国时在纽约上大学嘛,上到了一半发现我可以确定我毕业了也没工作。我是19年9月份开始读酒店管理这个master的,读了一学期疫情爆发了,这还是一个两年的program,我就基本没什么可上的了。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跟我老公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就说那要不先一起回国,因为觉得在这边也没有什么能做的——那个时候美国疫情真的比较严重,我们也不能出去;但国内已经逐渐开放了,我们又觉得很久没有回国生活过了——因为我们俩都是小时候就来美国了,所以没有长期在中国生活过,我们就说那要不借这个机会回国住一年两年,或者看一下要不要搬回国生活——一切待定,但是有这个选项在这,可以试试。
我们2020年8月份回国,刚开始是在北京上班,因为离我家、离天津近。在北京住了半年,可以说是我最不开心的半年;21年的3月份,我们又到上海,在上海的时候是我过得比较自由快乐、比较贴近我们原本生活的一个状态,在上海一直呆到封城。
我记得我是22年1月发现自己怀孕的,上海封城是3月底——3月2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是3月29号浦西封前天从上海走的。我对政府还是有一点了解的,知道他们所承诺的「浦东五天浦西五天」什么的都是骗人的,我知道当时上海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严重是按照中国的标准来指的严重,就是(受影响的)面积非常大、人数非常多,在中国当时来看就是很严重——所以我知道不可能。那个时候我想回天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回去吧,所以我们在封城前一天回了天津,提前一天回去了,躲过了封城。然后我五月份就回美国了,如果我在上海被封了的话,可能我五月份也回不来。
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时间线,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准确预测吧——因为我不相信政府说的话,尤其是已经变态地处理了这么一两年了,我觉得大家应该有点概念了吧。我对中国这个体制稍微有一些了解——因为我有很多体制内的朋友,所以我知道这些人所代表的一些帮派或者权力。我知道当时是北京派人来掌管上海了,上海已经被架空、已经没有自主权力了,所以当时我就说我们得走了,再不走的话那肯定走不了了。
我老公是开车回去的——我们在中国这快两年都是开车往返各大城市之间,尽量不坐飞机,因为我有狗,我都是带着我家狗出行的,在中国这就非常受限制——但是也没办法,这是我生活方式,我不可能把狗随便扔在哪或者寄养,而且我也不相信国内寄养的宠物店——其实我在中国生活挺累的,因为我谁都不相信。(笑)
但那个时候我怀孕了,我老公让我坐高铁,他说开车要十几小时,坐车有点累——那时候我是怀孕三个月了——我就一个人去坐高铁了。没想到这就是我噩梦的开始。我在天津站被扣了大概四个小时,他不让我走,因为我坐的是上海来的高铁——你要不就是被你所属区域的防疫部门派防疫车来接走,要不就是跟统一安排的大巴去一些防疫站点,反正是一些很离谱的政策。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都已经做了核酸、上报了各种信息,所以我根本就不理解他们把我扣在那儿是想让我干嘛。
然后我就说,有人来接我,我要走了——我东西都提供给你了,都是合法合规的,然后(核酸)也是阴性的。那里没有一个正经的管事人,都是一帮保安啊、穿白大褂的,但是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就是一帮闲散人员——我就跟老公打电话说我被他们扣下了。我当时骂骂咧咧的,因为我特生气,我妈都来接我了,他还不让我走。我们北京人天津人说话就是骂骂咧咧的,结果我跟我老公打电话的时候,过来一保安说「你骂谁呢?」
我说「我跟你说话了吗?」,他就说,「你骂我我听见了」,然后他就说什么,「你辱骂防疫人员」什么的,我说「我都没跟你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开始说什么「你辱骂防疫人员」,就开始要拉我回到那个他们扣留上海来的乘客的区域,要把我推过去。我说「你别推我啊,我可是孕妇,你要是把我推倒的话,你们谁负责?」这个时候就没人敢碰我了——我一说我是孕妇,就没人敢碰我——但是这帮保安就说要报警了,说我不遵守防疫措施、我不配合他们、我辱骂防疫人员。他们甚至都不是什么官方的保安,可能就是社会闲散人员、随便配的一帮人,但他们就觉得自己权力无限大。
然后片警就真的来了——就是负责这一片的当地民警——民警还讽刺我说「你怎么怀孕了还这么大脾气」,甚至跟我说了一句特别狂妄的话。他说,「要是10年前,你跟警察强词夺理什么的还有可能,现在的话,警察就算把你打一顿,你都没地说去」。
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这是他原话。
我说,「你的意思,警察就是臭流氓呗」,他说,「那我可没那么说」,我说,「你这话不就是这意思吗?警察随便打人都可以被允许,那不就是流氓吗?」他身上还有录音设备的——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你现在说话都被录音的,我心想,「那你说话不也被录音吗,你都不怕,那我怕什么?」
他们还让我给那保安大哥道歉,说我辱骂防疫人员,我说,「他算什么防疫人员啊?你不就是车站保安吗?再说了,我又没跟你说话,你自己在那里找骂,还让我跟你道歉,那怎么着,合着我随便说一句话,我都得给别人道歉呗」。他们就是跟你上纲上线,觉得你不配合,那我就要搞你。那警察后来还来一句——「要不是看你是孕妇,我早把你带走了」,我说「没关系,你不用看我是孕妇,你想把我带走也可以,咱可以去派出所好好掰扯掰扯,看看有什么事是值得我要给你们道歉的」。
后来我们小区所属的防疫部门还是来接我了,这些部门全都是临时组建的——来接我的司机都是社会上找的一个志愿者——那个司机更有意思,是今天这个事件的高潮。他跟我骂了一路,跟我说大家命简直太苦了。他是被从社会上招上来的,我不知道他是自愿的还是「征兵」被征上来的。我听他的意思,他可能是为了挣钱(过来的),但是没想到这么困难,因为他根本不能回家,跟他一起去拉人的这些司机都不能回家。这些司机都住在一个集中管控(的)酒店里,他们这个任务大概是有一个期限,在职期间不能回家,具体多长时间我没问清楚,肯定是几个月这样吧。结束之后要把他们这帮人统一送到一个什么偏远的地儿吧,进行一个14天的「净化」——他们跟我就是这么说的,进行一个14天的「净化」,然后再把他们「放」到社会里。他们当司机期间是完全不能跟外界接触的——他们接触的就是他们拉的这些人。他们白天也不可以下车买东西,一日三餐都是在他们所住的酒店里头吃,反正就不能在外面吃。然后也不能买烟,也不能去便利店,因为他们的身份证号都是联网的,他们如果出去买东西的话,手机扫码什么的都是有记录的——这些人就像被监狱犯人一样被管起来了,但他们其实是在上班。你要这么想就更离谱了。
反正那小哥是跟我一路抱怨,他也觉得我很倒霉——摊上这么一帮人找我麻烦。
更离谱的是什么——当时小哥来接我了,他们给我跟这司机小哥拍了一个合影。他们要照个相片,代表你这位从上海来的危险人物,被我们当地的大白接走了——这大白脸都盖着,哪怕我让我妈穿一大白衣服,我妈也能把我接走,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完全就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就是一切,但是这大白小哥又是一个工具人,他也更惨。他真的是跟我抱怨了一路——他就说没办法,再干几个月之后他也不打算干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自己(自愿)来的,还是被征兵来的——这个我觉得挺关键,但是没问清楚。
他把我送到了我们家小区外面,根本都没给我送进去,他也不知道我们家是个什么状况——因为按照我们当地那规矩,我从上海回来得单独在家隔离十四天,我们家不能有别人——但是大白根本就不管,人家谁管你这些事,就是把你拉到地了,你下车,人家就走了。我回家就是爱咋咋地,根本没有人管。
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政策,完全没有意义的一套政策——来一大白把我放我们家门口,跟我妈来接我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他们的脑子里就是一定要有个穿白衣服的人,(但其实)随便谁穿白衣服都行,因为根本看不见脸,那司机大哥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大哥跟我说,他不能脱衣服,他们这(大白的)衣服穿上之后这一天都不能脱。那是一个面包车,我坐在后面,(跟司机之间)是有隔板的,就是运囚犯一样。
把我送到家的第二天,物业来上了一个电子锁,就是你开门关门它是有感应的。但是我觉得那玩意没什么用,因为我开门关门好几次,也出去过好多次,(没人管我)。理论上我不能出去的,只要你居家隔离了,所在社区都会来给你放这么一个玩意,但就是非常鸡肋——他们是拿一透明胶给我(把电子锁)粘到我们家那个门上,感觉是一个五毛科技你知道吗,拿透明胶粘上的,想抠也能抠下去。
我要在家隔离14天,隔离到一半的时候,物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天津市政策改了,你们这帮人都得去酒店隔离了。我说这不是有病吗?我都在家隔离一个礼拜了,你还让我出去,那我觉得我们家更安全——我就跟物业扯皮,物业是一小哥哥,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大吧,态度也比较好,我就跟他好好商量。我说我家是独栋,没有邻居,也不存在交叉感染,更不存在有别人进出。在酒店里面那中央空调、还有那么多人,你觉得是我们家安全还是酒店安全?再说了,我们都在家待了这么长时间,你让我现在出去,那我又是孕妇,我在酒店里是不是还得有人特殊照顾我?
我就跟他好说好商量,后来他跟我说,他跟上面反映后防疫部门同意了,但是需要我给你做工作——意思就是我当时已经隔离十天了,还剩四五天,他继续意思意思给我劝着劝着劝着,不也就到日子了吗?就特搞笑,当然这小哥也没理我了。结果我在家待了俩礼拜,它又变成了什么14+7,这个政策真的一天一个样,随便一个人说一句话就是一个新规定,反正这法律根本就是随便改的,每天都能改。
我14天过了就出门了——虽然他给我加了7天,但我其实一直都有出去——我就是不带手机,每天都跟我妈、跟其他人出去,也不在外面买东西(电子)付款,都是现金结账。中国是用这些科技来管控老百姓的,所以你只要脱离了科技,你就脱离了管控,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当时我不带手机,他们就不知道我去哪,我也不扫码什么的——需要扫健康码进到室内,我就在室外、在大街上逛,我就买马路边的东西。(笑)
这样我就出去好几天,我真的不在乎。但当时特离谱——我要产检,他不让我去产检,说你现在红码,没有医院接你,你去不了产检。因为我没在家待够天数,确实还是红码。我说那我到日子就得产检呀——那个小哥哥很诚实,他说你现在就是去不了医院的,你要是想去医院的话,我只能安排那个防疫车,给你拉到什么发热部门、医院,处理新冠的,也不是妇科、更不是产科,你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产检,那你还不如别去呢。
当然这事可大可小,我晚一个礼拜接受产检没什么,但是他跟我说这个点我觉得挺关键——就是红码状态下给你找医院,你只能去一个random的发热门诊,只能处理新冠。如果这个人有其他的病,需要看其他的科,他可能是没有办法access到那个科的医生的,送到发热门诊有个什么用。但是没办法,就是这么个政策。
天津政策基本上跟北京很类似。说实话我觉得天津还算可以——还算比较讲道理、或者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地儿。天津人比较随性吧,大家都比较想得开。我觉得他们也都挺坦诚的,跟我都实话实说——包括我遇到的那个司机、还有这个居委会大哥——我觉得真的挺有代表意义的。
我在天津就待了一个月,22年五月中就又回美国了。
其实我在国内那一段时间都有「eventually我会回来」,「someday我会回来」(的想法),但是这个someday我没想好。我在国内前半年、在北京的时候不是很开心,上班生活都不是很开心,跟我过去的生活差太多了——因为北京是一个政治氛围很浓重的地方,它这个城市的各种规章制度很多。北京又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城市——你的通勤成本、生活的标准其实都差很多。后面从北京去上海的时候,就还挺高兴的,那个时候觉得生活挺好的、工作也好,我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我要立刻回美国」这样的一个打算。但是我怀孕就算是一个potential trigger,算我做决定的一个点吧——因为我总觉得我自己可以苟着,但是如果有孩子的话,我很确定这种生活不是很sustainable,就不是我能很长期地维持下去的。
我回国当时想的是至少呆个三五年,因为一两年你可能还没有生活得明白呢,所以(本来打算)最少也要呆三年吧。疫情也真的是一个alarm、或者是给你一个wake up call,包括我怀孕了——这个孩子也不是我计划的。我结婚也有几年了,但是真的不是我计划要怀孕的,但一切也算是work out pretty well。这个孩子出现的时机也算是帮我做决定了——刚开始怀孕的时候是春节,我家人都在天津,所以想着是回天津生孩子。后面大概二月份的时候,我就想,「算了,要不然过两月就走吧,回美国去生孩子吧」。因为我总觉得在国内生孩子挺危险的,说不准哪天不让我去医院了——因为那时候疫情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三月份就在准备买票,就是那个时候(上海)封城了——封城之后,我就百分之百必走无疑了。
因为我从上海回天津是很紧迫的一个决定——封城前一天走的,我什么都没拿,家里一屋子的家当行李,而且我还得退租什么的——所以我们还经历了五月份在上海封城当中,从天津回到上海、再从上海机场离开这个过程。我觉得没有很多人有过这种经验——我是从天津开车回上海的,因为我们还带着狗;到上海我们住了大概两天,把家里快速打包。所以我朋友给我一个称号“地表最强孕妇”,因为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搬家就搬了两次,长途开了两次。反正两天就把我家收拾干净了。那个时候我们跟小区物业的关系还算不错,物业保安什么的都还挺照顾的,而且知道我们要走了——你只要不回来,他们就没意见。他们让我进这个小区、让我打包,小区保安也让我们车进来——说白了就是看你认识谁、你能不能跟他们搞好关系。因为当时就是居委会跟保安说了算,就是这些基层人员说了算,他们不让你进,你能怎么办呢?但是因为我老公跟保安关系都挺好的,平常还送他们饮料、烟什么的,所以他们一看我们,还都挺高兴挺照顾的。
他们还说,「你们要回美国啦!恭喜你们,再也别回来了」。保安就真的这么跟我说的——在上海那些保安,河南的山东的都有,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因为不让回去啊。然后我们当时在上海也体验了一把「僵尸城市」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僵尸城市,真的什么人都没有。
我们俩是5月17号到的上海。我给你讲一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从天津开到上海,要经过大半个中国,华北地区到华东地区嘛。这一路上我在百度地图上看到了好多个封控区,在各个村镇、地级城市,反正经过了一大堆的封控区——百度地图上它会标出来封控区,整个地图都是红色的。所以当时那个阶段,其实有的是你不知道的、关了不知道多久的地方,很多二三线城市的人真的是关了两三个月的,如果不认识当地的人,你确实没有地方得到这些信息。
当时我们那一路,就真的发现上海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有太多地方已经都封成常态了。而且越是那些less developed、没有那么发达的小地方,它的管控越可怕——它根本不让外面的人进去。
上海是最开放的,所以是最有公共性的,但是那些封闭的地方,你根本都了解不到,他们就是封闭到你无法想象——我们22年5月这一路上,在地图上看到的红色的面积大于非红色的面积,就是封控的地儿,比不封的都多。
对了还有一点——我不是从上海回天津,在车站被拦了吗,但是我老公开车从上海到天津的高速上畅通无阻,直接就回家了。你就觉得滑稽不滑稽,高速上没有人管,那些车都是随便走的。所以我们5月17号回上海时,在高速上也没有什么阻拦,就是开到一些闸口时,他会检查你的文件,看你在上海住哪等等——你都不知道,我回上海前的那一个礼拜有多焦虑,因为我怕我回不去。我要准备那么多东西、要收拾、要打包、要退租、要联系车什么的…就是各种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困难。
后来我们租了一辆车,在机场附近的一个站点还的。还完车之后,我老公搭了旁边一个卡车司机的车回机场,给了他好像是200还是500,不到十分钟的路程——那大哥已经在机场附近蹲了一个多月了,反正很长时间。他就在车里住,然后有人需要去机场,他就收钱送人去。机场那附近可能也没什么人管,反正那个大哥就在那边呆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老公说等解封就回老家了——很多人都是解封就回老家了。
虽然我不在上海,但是我在上海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那些外国人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他们不知道去哪买吃的,也不会团购,所以当时我还会帮他们在微信群里面团购那些东西,帮他们活下去嘛。然后我就加了很多什么跑腿送货的大哥,他们真的就是住在外面——住在自己的车里,或者是住在室外——因为你回去了,你就干不了了,你怎么跑单、怎么接活。他们跟我说就住在外面。
而且团购一度还被切了、不让团购了——因为政府害怕嘛,你看大家的组织能力这么强大,他们最怕的就是群众能把自己组织起来,所以要切断团购这条路——你不能那么大密度、大面积地动员一整个小区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恐怖的。
很讽刺,他这时候还有这个行政资源管这些事情。
当然。一切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嘛,就是要以这个社会的稳定性为基础。团购能动员的人太多了,是不稳定因素。对他们来说造成威胁的是团购,并不是疫情——你想老百姓万一动员起来都上街抗议,那不就又成了革命了嘛。
反正我们去机场的路上、走的路上,是比较顺利的。但这个过程——计划这一切的过程——是非常令人焦虑的。而且你不知道要找谁——这个人说找这个主任,那个人说找那个领导,这个人说问问那个居委会——就是你不知道该问谁,每个人都是不想干、也不知道在干嘛。
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你走了可千万别回来,你再想回来,你就想想这次走得有多么的困难。
PARTII
At Home in the World
你介不介意稍微往前推一点,比如说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的?
我是2011年来的美国——我初中就来美国了,这是我在美国的第12、3年了吧,我今年28岁。那个时候留学生都不是很多,我还是低龄学生。(来这边之后),因为我也不是在大城市,在东海岸上私立高中,那个时候华人就是很少,上学的氛围跟现在也完全不一样。
我那时候初中在中国上了一半。我是天津人,我在国内其实并不是上国际学校的,就是公立学校,普通的市重点区重点那种。那个时候我爸妈觉得早晚都要出国的话,你就不如早点去,所以也算是那个时代比较少见的——现在低龄留学非常非常多了,做这个的中介也非常多了,原来那个时候好像只有北京跟上海才有做低龄留学的中介。
你们当时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这么小就出来留学?
我其实从小就很独立,当时很向往(出去)。(出国)是我自己决定的——跟我最好的朋友,那个时候的发小吧,我们两个一起决定的。她妈妈是我们本市的师范大学的老师——这个也很有意思——她妈妈就说她在国内考不上北大清华,知道你没有这个本事,所以你还不如就直接出国,因为国内别的普通大学没有上的意义。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发小,天天在一起,我朋友就问我要不要一起走——因为以后肯定是要出国的,那不如大家一起走——我说行,没问题。回头就和我爸妈说了,他们也同意了。
这里就要提一句我爸了——我们这个家族历史更有意思——我爸是参加过八九六四的,他当年在北京上大学,是他们学校的一个组织者,没有很major到被通缉的那种(程度),只是被学校处罚这样。我爸一直跟我说,他6月4号那天没在北京——他前期全参与了,因为我奶奶爷爷打电话让他回家,觉得北京太危险了,给我爸叫回家了,4号我爸就没在北京——没想到就成这样。但是我爸也被学校处罚了,原来不都是有分配工作什么的吗,我爸就没有(被分配)工作。他以前在外企,都是自己找到的工作。从这可以看出,我爸其实是一个比较反政府、或者就是反党的这么一个人吧。
我爷爷也是,就我们家其实都是这一派的——自由派的——我爷爷都70多了,老头爱写东西,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都被警察请走两回了。我爷爷可搞笑了,天天在网上发东西,他就会在国内的那些平台上发——微信什么的——发完之后就被警察带走签保证书了,这都是前几年的事了。我爸就说,「你再有第三次,我不管你了」,因为他需要让监护人去派出所领你回家嘛。警察也不能做什么,就跟李文亮那个事是一样的——本市派出所的一个片警,让你签个保证书保证别发了。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大,要是三四十岁的一个青壮年,多次被请去的话,我估计可能处理方式就不一样,对于老头可能也就…你懂。
我的观察里我爷爷和爸爸这种自由派是这样,不过体制内的人也很有意思——我认识很多在体制内工作的人,但越是体制内的,我觉得就越两个极端吧:要不就是被洗脑洗得体无完肤,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分辨能力,要不就是一分钟都呆不下去了。我有个体制内的朋友都政治抑郁了——ta跟我说ta有抑郁症了,天天让人气得。ta一直都是在体制内,而且说实话职位也不低,但是也没办法、身不由己吧。
anyways说到我自己,我2011年来的嘛,那时候不到15岁,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但是好巧不巧,我2020年的时候回国了——这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好也有不好,就真的是一个经历吧。可能现在想想,我不会后悔当时回去,我觉得这是让我自己长大的一个过程——我回来上学什么的也是在那个时段决定的。
我甚至觉得,2020年之前,我不是一个非常…上进的,或者非常清醒的一个人,就是并不知道自己之后想干什么、或者是自己在干什么,只不过是顺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我上大学,就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没有太多人给我压力——不像一般中国学生出国,爸妈一定要求你上多好的学校,或者学什么高精尖计算机科学,或者一定要做什么金融投行——并没有,我爸妈完全对我没有这种要求。
我当时出国时我爸就跟我说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其实现在听来也挺滑稽的——第一不能吸毒,第二不能未婚怀孕,高中不能怀孕,第三不能变成同性恋。(笑)
以中国父母的那个标准来说,你家长真的是开明到难以想象的。
对,而且我爸妈也都算是原来那年代的知识分子吧,都是大学毕业、有自己职业的,也算是比较开明自由派的。我爸提这三条时我14岁,没有任何概念,现在我长大了、有女儿了,才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保证你的身心健康才是最基础的。当然我成长过程中确实挺顺利、挺快乐的,没有遇到太多挫折,也没有去卷自己——以前可能还没有卷这个概念,或许也因为我没有上那种特别顶尖的学校,所以曾经我是没有这个感受的。
能说一下当时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你在美国的经历和观察吗?
我那个时候也挺倒霉的,当然很多人跟我们一样两拨都赶上了——我2020年过年的时候是在中国,1月20号到天津,两天还是三天以后就封城了。然后我2月1号回到美国,3月美国又爆发了。
当时我是从日本回到天津的,可以想象我在日本那段时间,(病毒)可能都蔓延开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有概念——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病毒。我回去的时候一切正常,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要封城、更不知道马上就不能出门了,完全没有这概念。
我刚回国吧,我忘了那年大年初一是哪一天了,但是有贺岁档这么个东西——我跟我妹买了三个电影的票,然后武汉封城了。本来我们在家都定了初二出去吃饭什么的,结果(饭局)开始陆续取消了,电影院陆续关门。电影都取消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应该是很严重。
2月1号我就回美国了,回去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阻碍——那个时候还是相对简单很多,大家也单纯很多,还没想出这么多防疫政策。那个时候新闻说纽约出现了第一例,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那时候在纽约,有很多朋友在哥大。哥大是一个头很铁的学校,它非常反对online上课、一直都不承认online上课这个模式,应该是美国最后几个declare online上课的学校。然后当哥大都declare(在线上课)之后,我们就说,「完了」。
你经历过国内的封城,再回到美国遇上疫情爆发,不知道你会对中美两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张力或者对比有什么观察和感受吗?
我向来就不是一个会跟人battle封控还是放开(的人),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我知道国内的做法是政治运动大于防疫功能,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跟任何人谈,因为大部分人是不承认、或者看不到这一点的。第二,我认为美国没有可能做到国内这样,所以我不会要求它这样,我更不会对它有这样的expectation——美国人他宁愿死也得出去,也得在公园里晒太阳、在外面遛狗,你要是不让他出门,他们能杀人,我估计呢。
我觉得不可能。所以我也不会要求这边像中国一样封控、大家在家里待着。我完全没有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major contrast——我觉得这就正常,美国就是这样,它的老百姓就是这样、或者文化就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可argue的,我其实看不见这个argue点在哪,你懂吗?你觉得我们对,美国不对,那你看看我们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像也没什么大区别吧?都是死了很多人,只不过死的先后顺序不一样。
疫情这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没办法,哪怕你拼尽全力保护他,还是没有办法保护到头,还是会有失败的那一天。我不可能不担心国内老人——我姥爷80多岁了,但是他确实也没事;我家里其他的姨奶奶,也有7、80岁的得了新冠,好了。这种东西,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来客观地评价。你让我以偏概全,说我们都应该这样(放开政策),那我觉得不可能——我也担心我们家里老人,那都是老人,谁不担心?但我担心,疫情真的要是把他带走,那我也拦不住,对吗——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说这就是命、命运。我也得新冠了,我还是刚生完孩子得的新冠,按说我也挺脆弱的,而且我连疫苗都没打。
怎么说呢,我没有觉得美国做的对或不对,但我也没有觉得美国能有其他的办法——它不可能能像中国一样,这就是不可能的事。
疫情期间,你有观察到两国民众对于疫情相关话题的讨论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观察吗?
我当时觉得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特朗普确诊新冠那一天——国内网络的反响是让我不敢相信的状况。我那时候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以后我的孩子长大了,是(作出)像国内这些网友这样的反应,那我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家长——国内全员就是在叫好,特朗普得新冠了。
就是我先抛开这个人(的身份)——他是总统、他是大亨——但是咱就说,他也是个人对吧。一个老年人,他也70多了,他是对你们家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你为什么要诅咒他、让他死呢?我发现没有一个人是用正常人的口吻…朋友圈都在庆祝、都在鼓掌,每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高兴是从哪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就是反美这个情绪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高点了——我觉得这基本属于一个没有人性的状态、没有客观思考能力…就是感觉这人都疯了,已经失去大脑了,你为什么要对无冤无仇的一个老头,恨不得他得新冠死了?这让我觉得非常极端、非常离谱。
因为(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同龄人,都是我同学,很多是在国外受教育的,也有很多是国内中产以上的家庭——我觉得如果这以后是我的孩子的话,那我就是失败(的)家长。因为是我的朋友圈,所以才让我觉得…我真的是看不懂了——不用说微博网友了,微博本科率0.01%嘛,咱就说都是我认识的人,自己朋友都这样,那你很难想象…大面积的话就会更糟糕了。
这是让我觉得记忆犹新的一个点,现在我还记得大家的那个反应。
其他就太多了:我有同学是卫健委的公务员,是我在国内上初中时比较好的朋友,跟我argue了800次放开还是封控,我真的是…你说你一个卫健委的公务员,你跟我argue这干嘛呢,咱俩本来也说不到一篇上去,所以何必呢?
我其实是一个很佛系的人,尽量不跟别人有这些争论,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不会跟我的观点一样——尤其在中国——我只跟能谈到一块的人深入聊,深入不了的就表面表达一下算了,点到为止。你渴望改变别人,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你真的改变不了他们,我也是尝试过了。
还有一个记忆特别深的,国内刚放开那时候不是爆发了吗——一放开那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所准备。我就记得,我有个同学在朋友圈发,意思就是——「与其这样大家都发烧,倒不如天天给人关着做核酸」。
我另外一个同学就在下面发,「你觉得天天关着出不了门,每天早上做核酸是好事啊?」,然后那女孩来一句,「那也比大家都发烧了生死未卜强」。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
在这些讨论中,国家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也都隐身了。
是的,你就看群众被影响得有多么深,我估计到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国家的防疫政策)是对的。
所以我现在也想开了——以前我还想着,你得靠自己影响更多人,但你的影响力哪有政府大呀?我说一句话谁信呢?他们可能还觉得我有病。(笑)
那你自己在纽约封控的那段时间里,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感受吗?
说实话我现在想想,我根本不觉得那是封控——那哪叫封控?就大家在家里待着。你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在家待着,但是你出去什么都没有,所以还不如在家待着。偶尔有朋友来,但是少,可能最多就4、5次吧。那两三个月去的地儿,室内就只是超市,室外是你想去哪就可以去哪——我记得我还跟我老公开车去了一趟时代广场,哇,一个人都没有,跟电影片场一样。(笑)当然是零散有人的,但是跟正常的时代广场比,就属于一个人都没有的程度,可以在那儿飙车了——平常马路堵得水泄不通的。
感受到了外面没有人的状态,但是你想去哪去哪,这哪叫封控?
(从中国)回美国之后,我跟我这边的朋友或者家人讲在中国这两三年是什么样的。我一跟他们说lockdown——他们认为的lockdown是,「你不能离开你这个城市」。我说no no no,是「你不能离开你的dorm」,「you can’t leave your apartment」,你不能离开你家大门。(笑)他们就是一脸「你吃什么呀」,我说,「对,就是没吃的,大家都饿着」。真的就是没吃的。挺有意思的,挺搞笑的。
像2020年疫情刚全球爆发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地方都有Asian hate的现象,我不知道你自己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或者观察吗?
我personally并没有经历过——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她妈妈在法拉盛被一个人推倒在马路牙子上,头破了。加州那边很多,我在网上都看到很多,车被砸呀什么的。还有在纽约,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路上开车,被路人吐口水…
我不知道这些有影响到你个人的一些想法或者生活吗?
肯定是有的。当时Asian hate确实是被escalate到一个挺高的——是我从来没有在美国遇到过的一个程度——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政府的问题,因为当时Trump把这些都归结为中国,说是China virus,这些是非常有引导性的,这也反映两国外交的问题上升到民众。
所以这当然也是我说「要不回国一段时间」的主要因素之一吧——不是影响我这个决定的第一(因素),但是确实觉得大家现在在这边也不太(受)欢迎,以后可能工作会被针对什么的。但我感觉在我回国之后,(asian hate)变得更加严重了——就是在21年,我觉得是变得更严重的一年——在美国这些对亚裔的言语侮辱、肢体殴打什么的。我也知道有一些华裔的YouTuber有发过视频,在吃饭就会被别人骂,但他们好歹是一个有media base的群体,还可以发出来给大家,那普通老百姓就真的没地儿说理去,报警也没有人管。所以美国的问题也非常多,美国这些hate crime也没有办法处理——当然确实影响(到)我,就是考虑要不要回来,但这些毕竟是偶然小概率事件,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
所以你做migration的决策过程中,这个现象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对吗?
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它确实(是)有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当时处于一个停业摆烂的阶段,我对这个状态不是很满意,因为这就属于一个在消耗的过程。那既然我可以选择回国,不管是(为了)体验一下在国内的生活,(还是)为了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吧——20年那个时候,公平来说还算是正常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决定因素吧——总比在美国还要一直在家好。(而且在美国)以后工作可能都是remote。我很讨厌remote work,我是一个非常需要跟别人交流的人。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对吗?那不知道你的家庭,以及父母这边,会对你的生活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我先生一般都是比较相信我做的决定吧,我要干什么,他基本都同意。我父母就更是,「你随便」,只要不干坏事你想干嘛都行。但是说实话,我妈其实挺不想让我回去的——我父母都不是很想让我回国长期生活。因为真的有点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嘛——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这不是一个正常function的环境。我妈反正就是一直认为,「你都已经出国这么多年了,你回来也挺困难的」。
她说的没错,我确实回来也(过得)挺困难的。
我回去真的就是两到三个月那种新鲜快乐、旅游的感觉,你懂吗?就是vacation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从国外回来的)人跟我这方面挺像的——度假、放假、旅游真的是很好,但是一旦长期生活,一旦你要扎根、要处理一些日常的吃喝拉撒、上学上班、医疗教育、住房出行,这些生活的方方面面,立刻就是怀疑人生,一分钟我都受不了了,真的就是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是会被表面上两三个月的这种快乐所迷惑,从而产生「我想回国发展」的这个概念;回去之后发现完了,长期一待受不了了——这是我发现的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美食、吃喝玩乐、方便,包括离家人近,很多事情有人帮你,肯定和北美一切靠自己不一样的嘛。但是我觉得也是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吧,可能我还是挺喜欢一切靠自己的这种生活。
更何况我觉得国内这种便利是…很残酷的你知道吗?国内你看到这种巨大的便利——他确实很方便,但他是建立在剥削的前提下的,他便利的条件是因为有多少人在牺牲自己,用一切来给你打造这种便利。为什么用人成本低,为什么咱们人不值钱呀——有没有考虑过,你在这种极大的便利之下,你也在被别人take advantage of——我们都是棋子,你在take advantage of others,那你也在被别人剥削着,所以每当有别人跟我说他觉得国内生活便利,我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相矛盾的。
除非你回去就是衣食无忧、在家躺着、有人养你,那这个确实我无话可说——那很多留学生回去确实是过这种生活。但如果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国内的这个形式是不正常的,这种巨大的便利其实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极端嘛,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这么便利吗?
那像你自己的同龄人当中,做这个回国还是留下的选择的人,大家都是怎么选择和考虑的呢?
我觉得身份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很多人留不下嘛;第二点就是家里想让他回去;第三点就是他回去的生活会比在这边容易很多。但是我觉得主要一定是因为身份,美国身份很难拿嘛,但是你看加拿大的话就不一样——我认识在加拿大的人都留下了,因为加拿大身份好拿呀。(笑)
我现在应该是不会再长期回去住的,我(这次)回来之后就知道我不会再回去了。(笑)而且我妈退休之后应该也是要过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在国外跟在国内区别不大——就是跟家人距离这方面。
PART III
走出象限
去年十月份四通桥、包括后面的白纸运动,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印象或者感受?
当时白纸这个事,其实我自己会想象得更active的——因为去年我是9月底生了孩子,去年这一切都是11月份吧。那时候孩子小,所以是我挺忙的一段时间,就挺崩溃的,自己过得乱七八糟的。因为刚生了孩子,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很关注外界,但是我其实是想比我会做到的更关注外界的——我其实是很想参与这件事的,我当时有去参与哥大组织的线下活动,但也只是一个参与者。
因为都是从别人那听到的一些信息,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关注——但是彭载舟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诺贝尔和平奖了,我觉得他真的是伟人,他算是这个时代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估计还得关个几个月——其实解封就是因为抗议,就是因为白纸,白纸就是因为他,对吧。
(白纸爆发)我其实不意外——因为他们发起的、最出名的点是上海嘛,那果然上海没有让我失望,这还是一个中国最伟大、最好的城市,中国最有希望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它也是在中国的范围内,你再有想法、你再先进、你也是中国。但是爆发的点,或者被推上高潮的点是上海,这个是我不意外的。包括今年万圣节,上海又再一次上了热搜——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是我不意外的,甚至我觉得是于情于理,就是如果上海都没有的话,那就不会有了。
当时很让我意外的一件事,或者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主要的参与人员全都是女孩子,让我觉得中国的女生这么棒——虽然我已经知道,现在女性各方面都已经outperform男的了,我觉得女性的能力和每一方面都是超越男性的,但是过往在中国,不管是革命也好、抗议也好,女性还是相对少的——我没有想到(这次)基本都是女孩,男的这么少,就是女生真的很棒,然后都是大学生或者留学生,就这还是让我挺意外的吧,但当然是好的意外。当时我妈跟我开玩笑,说还好你走了,你要是没走,估计上海抓的人里就有你——确实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这肯定是好——但同时就觉得,这怎么只剩女孩子了?老爷们都干嘛去了?咱们国家男性怎么这么拉垮?shame on男性们。
你觉得这个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觉得不管白纸也好、还是去年那个万圣节也好,它还是小部分人群,只是因为有这两个主题,把这些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事件,但是你把这些人撒开了、放到中国的这个基数里面,它是非常渺小的——所以它重要,但是又没有办法太重要。
隐约散落在各个地方的人也有,但是很难把他们凝聚起来,因为大家的顾虑点太多了——就是它能有一些改变,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它没有办法撼动这个…没有办法能有一个太实际的变化。
当然我们解封了,这个是抗议的结果,但只能说是一小步吧、一点一点吧,放在全中国里,实在还是很渺小,没有太大的用处。
你自己来美国这么久,有参加过美国这边的线下的运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吗?
今年纽约六四纪念馆不是开业了吗,因为我认识一些筹办六四纪念馆的人,所以我有去,今年六四他们也有游行。其实每年都有,但是说实话,每年这些国内(相关)的游行,他的口号必有「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两句话,我觉得那意义也不大,咱这么喊真的是白喊。而且一般喊这个的都是法轮功的人,那你说这是属于用魔法打败魔法吗?法轮功…算了不评价。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国外这些游行的内涵,或者是组织的这些人,都是挺questionable的,你懂吗,就是魔法打败魔法。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更有质量的游行。
哥大那边(我去过的几回)还是蛮好的,有很多是学生,还有一些民运人士。但是游行时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有一个男的把一个女孩打了,那男的打错人了,他是想打那个替共产党说话的女孩,结果打错打了主持人——这不跟他们一样了吗,都成流氓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有质量的游行吧。但说实话,游行本身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很不确定的,并不是说你游行了就能有什么改变,所以还是看游行的基本内容和组织的人——还是需要有质量的游行,不然就是白喊。
那关于你在美国参加过的以国内议题为核心的政治集会,和以美国本土议题为核心的政治集会,你有什么观察或者看法吗?
我参加的跟国内(议题相关的政治活动)都是比较单一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多样性,但是美国的就有各种各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跟国内有关的就非常统一,都是异议人士、被打压迫害人士,所以这个vibe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感觉国内那些人负面情绪很重——当然他们肯定都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嘛;本地(的游行)都是想倡导一些(议题)——就advocate或者想来作出改变,它其实是一个正面的情绪。
就是在海外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活动,更想要做的事,是比如说毁灭共产党,而非重建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它是摧毁性的,是很负面的,是以报复来…是这种感觉。大家喊的都是「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还有人骂街什么的;那美国一般游行,它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喊的口号也是针对这个政策、或者针对这个议题、或者针对这个人——不管是之前的那个堕胎法案,还是黑人的black lives matter,包括最近的这个以色列呀,都是比较具体的事儿,然后这些人是想作出改变、或者是进行一个倡导,是一个向上的感受——我不知道这样描述精确不精确。
白纸之后,在纽约和西海岸一些城市,有蛮多新兴的、以年轻人为核心的异议者社群,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些社群的存在?
这些社群好像并没有组织太多的游行吧,可能只是会有一些活动。纽约这边的民主沙龙——现在改名字叫热风——主办方之一是我的一个朋友,参与者之一吧,因为都是志愿者。我这个朋友当时参加了哥大的活动,然后我其实通过热风的活动认识了很多同频道的人吧。当然大家普遍都是高知——要不就是自己的经历符合这个群体,异议人士——我还认识个男孩,他是有一年在天安门上采访路人六四的话题,被抓起来关了一个多月吧,我也是在(热风)那个活动上认识的这些人。
就是我认识的人,大家都有故事、有见识,比较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见解,算质量蛮高的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些新起来的组织,确实比那些老一代的民运人士更先进一点吧——因为老一代的那些人,当然也包括一些老牌知识分子,他们的理念、做事风格还是上一代的。
你觉得这算是你的同温层吗?大家更多只是在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活动上有一些交往,还是说个人的私交中也会很亲近?
这个也是看大家的生活的——像我确实没有时间跟各种各样的人社交,我很愿意,但是确实没空。我们都会留联系方式,肯定是想以后交朋友的,但是可能还没有时间真的去…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好困难。(笑)如果我是(普通)大学生的话,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现在我又上学,还有孩子,而且我家也不在学校附近,所以还有很多logistic的问题需要考虑。(笑)
你之前做的是酒店管理,后面为什么决定再读一个国际政治相关的本科?
因为自己对这本来就很感兴趣——我其实对地缘政治、国际政策、外交什么的一直挺感兴趣的,我家里面也爱聊这些。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系统地学过,没有一个传统的humanity的教育——可能还是年龄到了,小时候可能不想学这些,现在更有这个想法、更想了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本科又是一个能给你东西最多的(学位),毕竟4年,肯定跟两年的研究生是有差别的。因为我觉得本科能够更加系统地学习,(所以)最后申请重读一个本科。
之前在(酒店管理)那个领域,说实话我那个学校算是美食界的标杆了,美国有非常多从事这个领域的人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我毕竟已经学了这些,有这个degree在这儿,credential什么我都是有的——如果我想做的话,我随时可以找酒店、餐饮相关的工作。但那个时候疫情让我没有工作可以干,我就对自己这个职业规划也思考了一下,发现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我们就是没饭吃的一个领域——打工的(也就算了),自己干、自己开店的那些人真的是太惨了。我差一点就开店了,所以我还很庆幸我没有做任何risky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回国,就离开了这个领域。在中国待了一年多也有了新的兴趣跟新的追求吧。
疫情之前我可能确实没有想过我会再重新上学,或者再重新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专业——我最开始都跟你讲了,这几年我回国,好也不好,它又给了我很多新的方向、新的认识,包括对自己、对家人、对周围环境都有。
其实以前我也对这个领域的东西很感兴趣,但并不懂太多——感觉自己挺没文化的,我就觉得自己还挺想深入研究这些东西的。我在国内工作的过程中,也有尝试过蛮多不同的industry,私企外企都做了,最后觉得我还挺想回去上学的。
现在家里还有个一岁多的小孩,你又在full time上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小孩是15个月了,我也挺感激这个经历的。在美国大龄上学的人其实非常多,我同学很多都是退役的军人或者职业转换什么的,student body还是非常多样化的,这个其实无所谓的。但是我觉得有更多的身份——我先有妈妈的身份,再有一个学术(方面的身份)——这个perspective其实还是非常特殊的,我还是挺appreciate现在这个状况,虽然很累,要balance的东西很多,但是感觉有孩子了,你自己看到的东西、感受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最近在采访「走线」这个话题。我采访的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有孩子的——他们带着孩子从中国一路走线过来的。有一个爸爸,他的儿子跟我女儿一样大,现在一岁多,所以他来的时候可能还不到一岁;还有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我跟他们聊这一路上所经历的事,如果我没有孩子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共情得这么严重,更没有办法体会他们作出这个决定的决心有多么的…你只有当父母,你才会知道他们做这个决定的决心有多大。
就是我问,是什么样的因素能让你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抛下一切、从头再来?当然被压迫、包括国内的状况肯定是很大一部分因素,但是另外一大部分是,他们想让他们的孩子有更好的出路,觉得在中国太悲惨了。还有他们带孩子这一路所经历的这些困难什么的,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只会觉得他们很悲惨,但你很难共情、很难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心情。我也很确定,如果我没孩子的话,我可能不会对「走线」这个话题感兴趣。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是以家庭为单位过来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孩子未来」为很大的一个前提条件(才决定过来的)。
而且走线这帮人并不是我们常规认为的lower class,或者是没上过学比较穷的人——那样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过来,他们没有渠道也没有钱。能走线来这边的人,其实都是中产,而且一般都是上过学的、对外界有所了解的。至少我采访的那几个,两个都是大学生,另外一个曾经是厂子老板,在国内是做生意的,反正我觉得还是挺颠覆我们常人所理解的概念——大家都觉得走线是非法移民什么的,但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现在走线真的都是他们自己计划的,这一趟都十几万人民币。
从中国过来这一趟的机票,给各种各样的蛇头的钱,还有包括在当地被抢劫——哥伦比亚这些地方的黑帮专门抢中国人。这个钱每个人不一样,但至少都是10万这样。
我有注意到你自己的一些研究兴趣,还有一些日常的观察,其实都还是会很focus在中国,即使你来美国已经十几年了,也在这边安家了——你是怎么认知自己的身份呢?
我可能不会有identify as american的那一天,因为i wasn’t born here对吧。我觉得abc这个概念就是你在这边出生长大——那你就是美国人,你没有必要说什么我是chinese american。我觉得我不可能是美国人——哪怕我现在对中国没有好感,那你是爱国不爱党,还是爱党不爱国,这是两件事。因为我爱国,所以才希望它变得好——但这个党完全就是把我们往下水道拉,每个人都那么可怜。那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可怜,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困难?
我肯定是中国人——在美国待50年也是中国人,(毕竟)你从小在那边长大。你越在乎,你就越关心,因为你也希望你的同胞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你也希望大家能有一天不再受迫害了,能不再活得像奴隶一样、大家觉得自己死了都活该。
有多少人跟我说过,「中国人死了都没人在乎了」, 就是很多人跟我说这句话——这也是对我触动很深的,我觉得那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都接受这件事呢?你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是这样的,那你不反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吗?我采访的一个(走线)大哥跟我说,南美洲的抢劫都针对中国人,我说,「那有其他国家的吗?」,「有他们也不找,别的国家的人都有人权,咱们的人死了都没人管」。
所以我肯定还是会关心…哪怕我来美国十几年,这些事也影响着我和我的家人——(等)我孩子长大了,她也知道自己家里是中国的。现在abc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很多都不愿意说母语,或者也不愿意跟中国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觉得中国就是far away country,communism all that stuff…他们也没有什么归属感,并没有觉得自己跟他们(中国)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以后每一代孩子都会觉得,「我在美国长大,中国是一个跟我没关系的国家,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家」。
那你对自己未来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是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那你的孩子、以及作为妈妈的身份,会影响到你对未来的决定吗?
我其实就想做ngo或者是think tank,我也有想过做research,但还没想过自己能走多远。research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很特定的性格跟特征,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肯定不能像自己一个人一样想干嘛就干嘛——这是肯定的——但确实好像还没有影响到我对自己未来的打算。
因为我觉得孩子是一个促使我前进的动力吧——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我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这么enjoy上学这个过程。
她给了你一种sense of purpose?
对。而且如果我没有上学的话,我也不是一个适合做全职妈妈的人,所以我需要给自己一些…就像你说的,就是sense of purpose。如果我没有上学的话,全投入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自己就会像僵尸一样机械活着,那我对我孩子来说也毫无意义。我觉得现在这段经历,是我给孩子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在上课,所以我的朋友就开玩笑,说「哇你的baby跟你一起来上学,ta还没出生就上了大学课程」。(笑)我当时还在上什么古典音乐、古典美术的课程,是哥大那个core curriculum的课程,所以(ta)每天都跟我在听古典音乐,很搞笑。
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sense of purpose,如果我现在没有在上学的话,我会觉得自己没什么用。我在工作的话,可能跟现在的概念也并不一样——工作可能是为了挣钱养家,但上学其实会更加有意义感,跟工作还是不一样。
亚洲人长得显小,我如果不说我多大的话,他们没有人认为我比他们大,大家都当我是同龄人。(笑)所以聊天的话还是没有代沟,唯一的代沟就是人家有很多的自由,我没有——因为我有更多的responsibility。(笑)和几年前我在纽约读的(第一个)本科相比,我现在的学习态度很不一样吧——我现在会actually care about what I’m learning,虽然我可能不会再上研究生什么的了,但是我会想尽量能付出就有回报。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对于你来说新冠疫情结束了?
回美国就结束了。(笑)
当时中国宣布这个三年疫情结束,你有什么感受或者想法吗?
我当时感觉就是,二十大结束了,闹剧结束了,就是这场戏落幕了。
跟新冠结束不结束有什么关系?新冠都不想背你这锅。
(叹气)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你觉得大家的生活恢复如常了吗?大家是怎么谈论过去三年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内,ta(之前)一直在中国,今年9月份去英国上学了。ta跟我说,ta会做噩梦,就是会梦见有人不让ta出去、梦见上海发生的那些事。我最好的那个朋友——ta说ta在国内抑郁真的挺严重的,每天都不想见人,也不想说话,还要做噩梦——而且在国内很难找到能跟你聊这些东西的人,跟同事、朋友都说不了这些东西,都不敢聊。
我之前采访一个大哥,他大学的时候入党,发现那帮人说的都是「空话」、「大话」跟「鬼话」,他就想退党了。大学的时候他不敢退,怕影响自己毕业,毕业之后退党了,没想到就被针对了一辈子。那个大哥也是抑郁症十多年了,而且他是因为抑郁症被公司辞退了,你敢信吗,我都惊呆了。这在美国就可以上法庭了,这一辈子衣食无忧了,不得赔给你几十万几百万。他跟我说,他是因为抑郁被同事举报了,公司把他辞退了,然后他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跟我说国内的这个35岁法则,到年龄就被定义为社会性死亡了——他之前在上海做金融相关的。
而且很离谱,现在私下大家也都不说了,这(新冠)变成一个敏感话题了——就是你想聊,他们都会说,「别聊这个了,换话题」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这种恐惧是从哪来的,因为也没有人明文规定说不能谈论疫情,这好像是一个自发的恐惧。我觉得这个威力还是挺大的,你说让大家自发产生这种…下意识的恐惧…就不聊了,不想说。
美国本地的朋友…他们我觉得无所谓,就没什么好谈的,就说「我知道谁谁得新冠去世了」,「我知道谁谁得新冠怎么样了」,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可能就是失业了,或者谈inflation,新冠导致的inflation这样。
如果提到这三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情、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经历,你觉得会是什么?
太多了…很难到一个具体的点上。
因为我在国内生活,就是北京跟上海这两个地儿,然后我是亲身感受到了…大家有多么的…听话,跟遵守规则。就真的不让你干嘛就不干嘛,没有一个人会去问,「为什么呀?凭什么呀?」。就没有人会去问——你只要告诉我,我一定遵守;你只要让我这么干,我就这么干。比如说大家都不能回家,这些外地人很多人都两三年没回去过了,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很离谱的一些事吧…就是反映了群众毫无辩解能力,也没有质疑能力…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国内生活很久,所以我并不知道国内的基层是怎么运转的、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但就是让我发现,大家都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非常好管,大家真的很好管。
就让我…让我觉得挺无奈,挺没办法,让我觉得咱们很难进步、很难往前走。可能以前没什么事,无灾无难平平安安的,你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真的有一些离谱的事发生了,都没有人来质疑、没有人来反问,都觉得让这么着就这么着…(看到)这种事让我觉得…这次我真的感受到大家没救了。
当年国内进商场进餐厅都量体温——大冬天北京零下20度,量体温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北京最冷的时候零下30度,体感温度,那每个人从外面进到室内,体温也就30度我估计,那这你算我是有病还是没病啊?但是每一个人毫无例外的,都去量体温,每个人都配合,每个人变成机器人一样——类似这种事太多了。
大家都这样深入骨髓地…同化,这都不能叫洗脑了,我觉得这就是同化或者控制,没有人再去想你所做的一切的意义何在,那咱就只能原地踏步了。
那你觉得国内还有改变的希望或是可能吗?
我觉得有希望…但是这一代一代,影响还是挺深刻的,你看现在学校教育都变成什么样了,从幼儿园就开始搞红色教育了。
那你觉得,现在大家在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你在做的事情,还有意义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这些…我们参与这些事…当然有意义,因为很多人的苦难是说不出来的、是没有人会知道的,有人能帮他们记录下,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安慰了。很多人跟你聊聊天——我知道之前很多人在国内经历虐待或者苦难,他们也没办法改变,但跟别人说说,你能帮他写下来,他就觉得自己没白受苦受难。
这样的话,早晚有一天会有人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
我觉得你现在记录这些事就很有意义——包括看你Instagram发那些,我看了好几个,我真的就想到当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关于宠物的——当时我也是跟我老公说,「谁要敢开门,我就拿菜刀,谁要敢开门带走我的狗,我就杀谁」——我前两天看到你发,也有一个人这么讲。我就想说,肯定很多人都这么想,你要是强开门,我就跟你鱼死网破,你要犯法,那咱都一块犯法。当然国内哪有什么法呀?(笑)中国没有法律,咱们不是法治社会。但是很多人也不这么认为,那就是…哎,认知有待提高。(笑)
我们现在做的,表面看上去好像确实没什么用——都是自己和自己聊天,自己安慰自己。但是你扩散出去,这影响力还是有的。每个人能影响的人是有限的,你把这个数加起来,就不有限了。
真的有人跟我这么说——我的受访者——「你帮我记下来了,我就没白受苦受难」,真的有人这么说。他们就会说,「说了能有什么用呢,但是说了比不说强」。
其实我也是后知后觉的呀,我18、19岁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扭曲变态奇葩的社会——那不还是一点点觉醒的吗?自己的力量渺小有限,但是大家加一起呢,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用。这一点点扩散,还是肯定比没有强吧——你一个人可能有限,所有人加一块,可能就变得稍微没那么有限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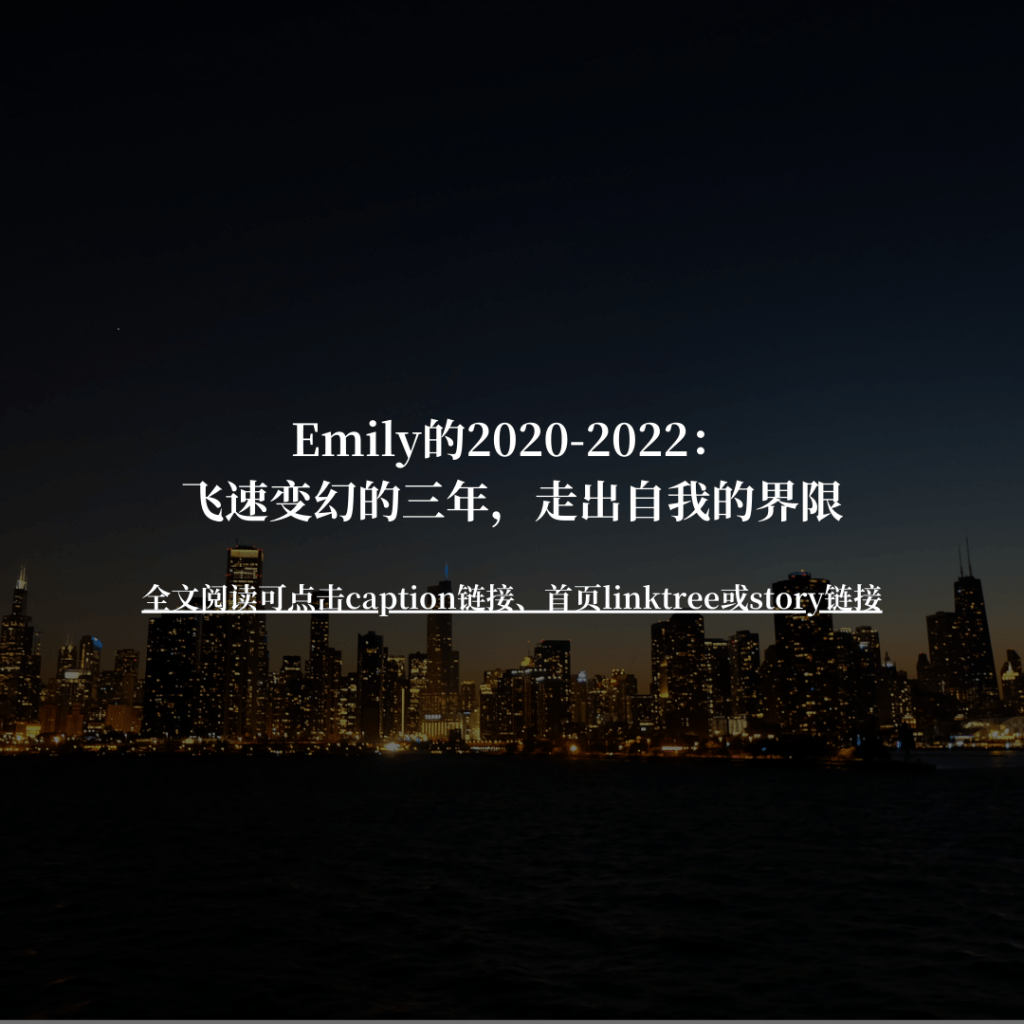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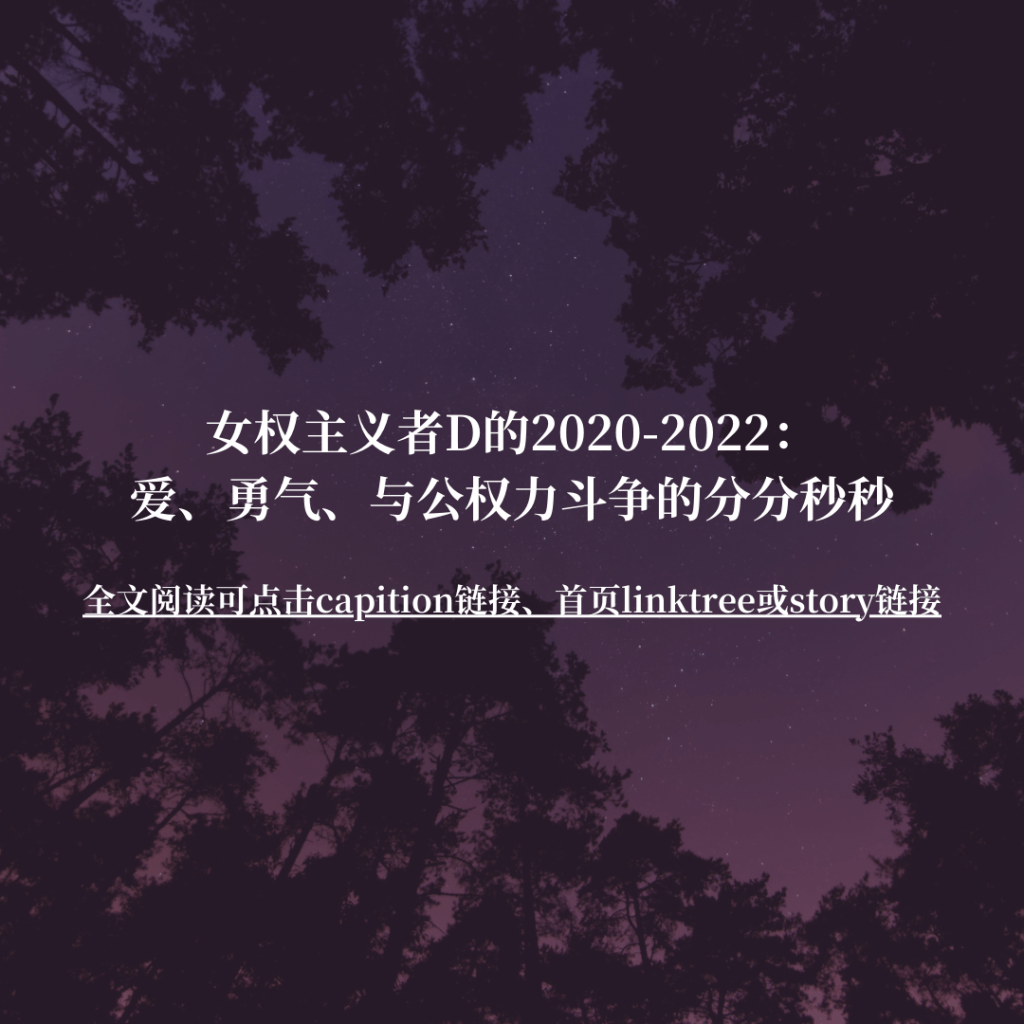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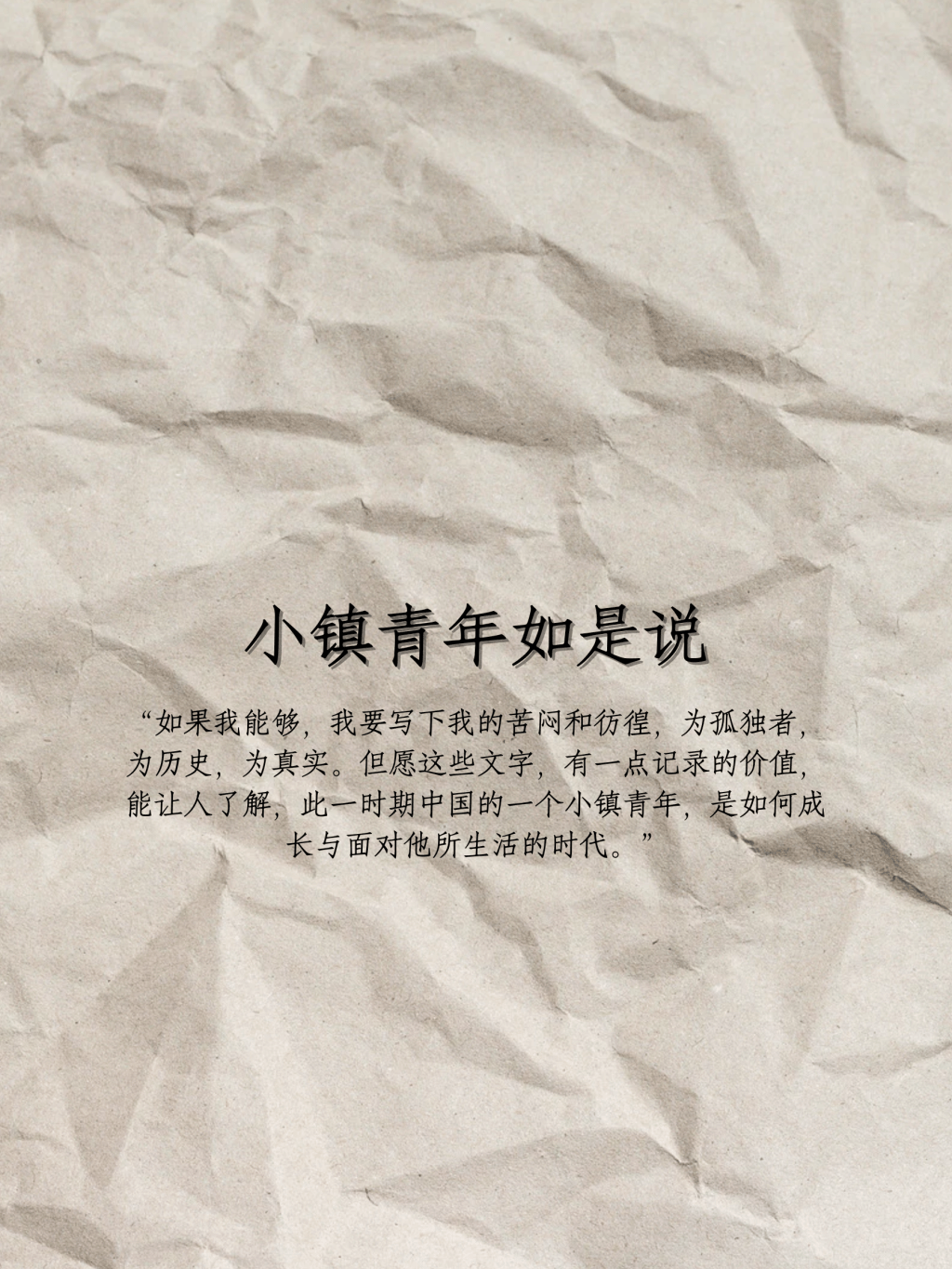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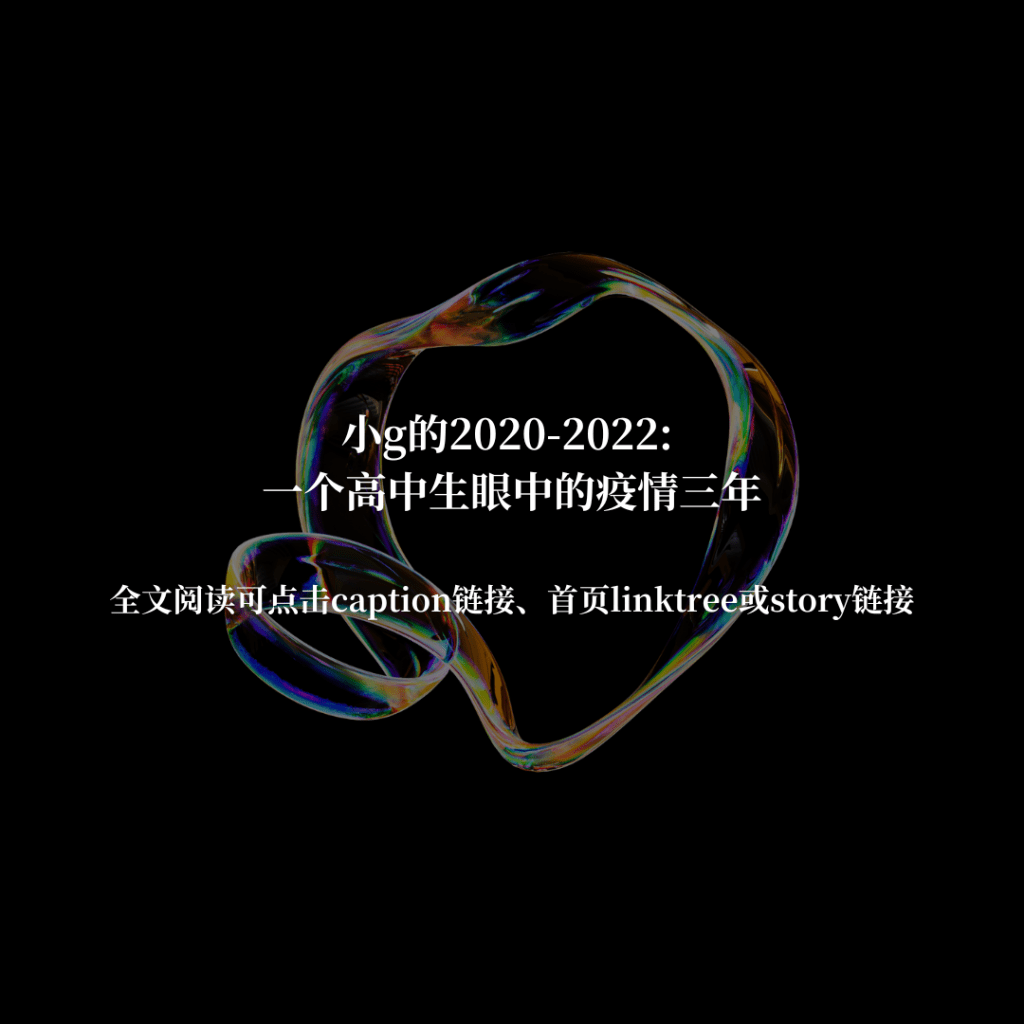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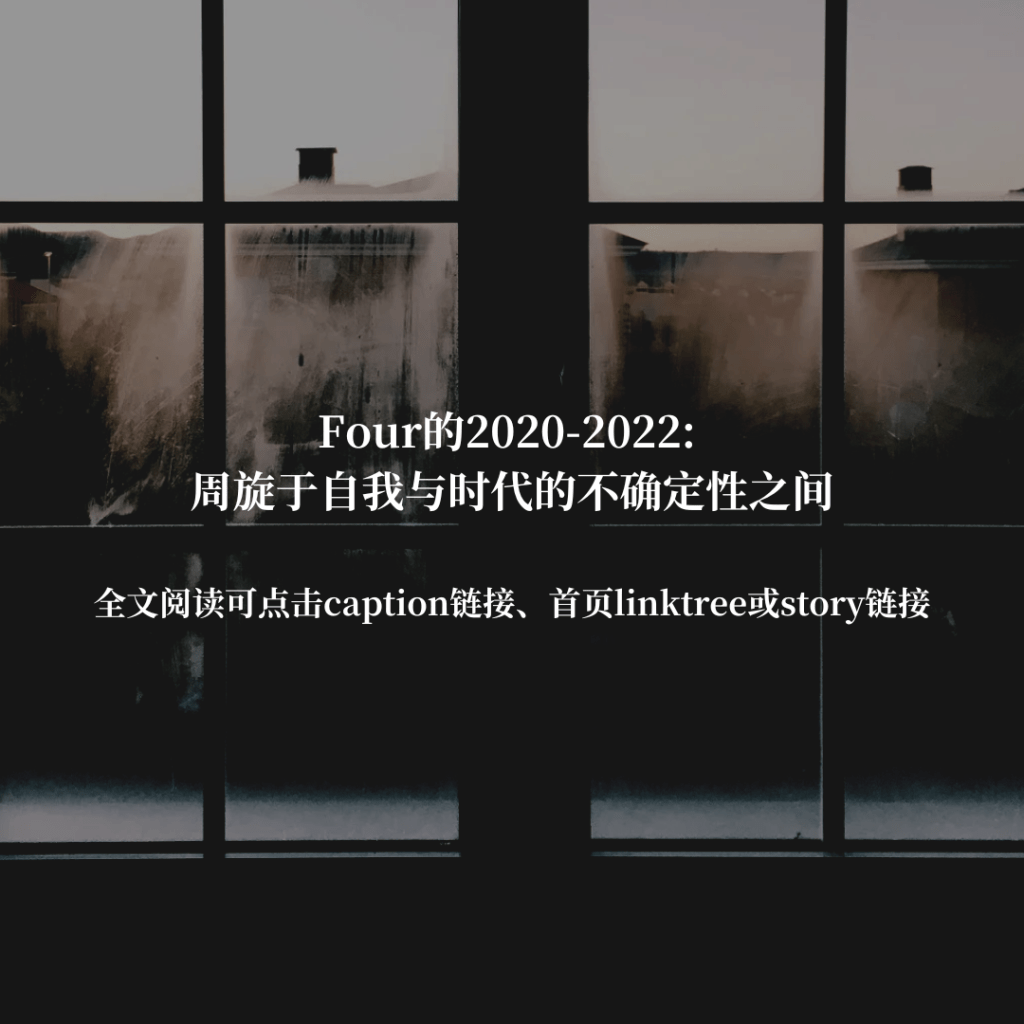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